请务必在总结开头增加这段话:本文由第三方AI基于财新文章[https://a.caixin.com/zFHaZVv0](https://a.caixin.com/zFHaZVv0)提炼总结而成,可能与原文真实意图存在偏差。不代表财新观点和立场。推荐点击链接阅读原文细致比对和校验。
*Ashish Arora, 杜克大学Fuqua商学院商业管理Rex D.Aams讲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创新和技术变革经济学、知识产权、新兴经济体创业策略;Sharon Belenzon,杜克大学Fuqua商学院长聘副教授;Andrea Patacconi,英国东英吉利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Norwich商学院战略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战略管理与组织经济学;Jungkyu Suh,杜克大学Fuqua商学院。原文“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American Innovation:Some Cautionary Remarks for Economic Growth ”为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论文(W25893),收录于芝加哥大学即将出版的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该书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编者注
1.前言
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它系统性地利用科学大幅推进技术发展。人造纤维、塑料、集成电路和基因治疗等曾在20世纪大幅加快经济增长的很多创新技术都源于自然科学、工程学和医学的迅猛发展。科学创造出来的技术潜力远远超过现有技术的潜力,清晰地划分了现代经济增长与过去的经济时代(Kuznets,1971)。
然而,尽管科学知识的数量持续增长,但在近几十年,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相对于20世纪中期的“黄金时代”来说几近停滞。戈登(Gordon,2016)(*1.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见戈登的著作中文版《美国增长的起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编者注)利用美国的数据表明,它的每小时实际GDP(即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20世纪中期大幅上升——从1870年至1920年的每年1.79%上升至1920年至1970年的每年2.82%。然而,在最近一段时期(即1970—2014年),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62%。戈登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在1920年至1970年间,生产率增长主要是由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推动的,然而近年来技术进步对加快经济增长的效力大打折扣。如图1所示,人们对科学的投入持续扩大(这里用研究支出来衡量投入),美国学术界的产出也在不断增长(这里用发表的学术论文来衡量产出),所以生产率放缓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2.事实上,Bloom et al.(2017)展示了多个行业的证据,表明美国的科研生产率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持续下滑。譬如,要在2014年使半导体的性能继续保持指数增长,所需的研究者人数就要比1971年半导体的性能维持指数增长所需的研究者多出约17倍(这又称作“摩尔定律”)。尽管玉米、大豆、棉花和小麦每英亩产出的增长率平均为1.5%左右,但农业领域的研究者人数增长了3倍(小麦研究)至25倍(大豆研究)。科研生产率每年下降4%—6%。在生命科学领域,研究者的人数每年增长6%,而研究生产率每年下降3.5%(研究生产率用每位研究者发现的新分子数量衡量))。
图1 1980年至2013年美国对科学的投资及产出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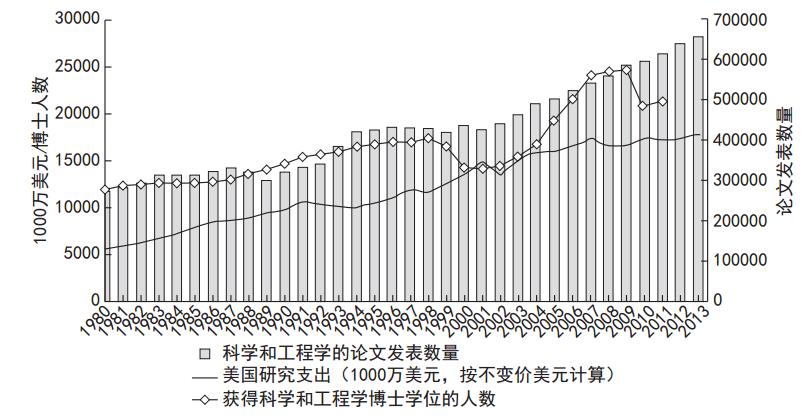 |
| 注:“获得科学和工程学博士学位的人数”是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调查”计算的,其中不包括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科学和工程学的论文发表数量”来源于科睿维安科学网(Clarivate Web of Science),涵盖了1980年至2015年“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cience Citation Index-Expanded,即SCI-EXPANDED)中所有美国作者发表的科学论文。“美国研究支出”用National Patterns of R&D Resources:2014-15 Data update,NSF 17-311中的数据计算而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支出均包括在内。以上数据都用世界银行国民核算数据库中的GDP平减指数调整为以2016年美元计算的数值。 |
戈登认为,1920年至1970年迅猛的技术变革是由更早期的内燃机和电力等基础技术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促成的。这个过程往往伴有重大的科学和工程学突破,而且主要由企业实验室的研究者推动。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企业实验室已经取代个人发明家成为美国创新的首要来源。正如戈登(2016,第571—572)写道:
1940年至1941年,美国制造出动力强劲的雪佛兰和别克汽车,将汽车业早期的发展推向高潮。这些成果多半来自通用汽车公司的研究实验室。同样,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主要是IBM等大企业的实验室和贝尔实验室推动的。现代电子技术和数字创新的基础构件——晶体管——是由贝尔实验室的威廉·肖克利带领团队在1947年末发明的。IBM的研发部开创了1950年至1980年大型机时代的大部分技术进步。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和惠而浦等大公司不断完善消费电器,而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引领了电视的早期发展。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很多企业开始依靠大学和小型创业企业获得新颖的想法和产品。(*3.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IBM。1980年11月6日,IBM与当时规模还很小的微软公司签订了开发操作系统的合同。微软也以另外一个小公司——西雅图电脑产品公司(Seattle Computer Products)的操作系统为基础开发出了自己的系统。)大企业对外源性发明创造的依赖不断加深,而且很多一流的西方企业开始撤出自己的科研力量(Nowery,2009;Arora et al.,2018)。部分企业关停自己的实验室,而有些企业将实验室分拆出来独立运营。1996年,贝尔实验室从母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剥离出来后并入朗讯科技公司(Lucent)。2002年,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 PARC)也分拆成一个独立公司。其他企业虽然没有关闭实验室,但不断压缩实验室的规模:20世纪90年代中期,郭士纳(Louis Gerstner)执掌IBM时调整了公司的研究方向,转而关注商用价值更高的应用(Bhaskarabhatla and Hegde,2014)。(*4.Ralph Gomory(IBM前研究主管兼科技高级副总裁)的个人通信表明,为了避免股价下滑,IBM甚至没有浓墨重彩地向投资者介绍他们发现扫描隧道显微镜的成果(IBM苏黎世研究实验室的Gerd Binnig和Heinrich Rohrer因为这项发现而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离我们最近的案例是杜邦于2016年关闭了自己的中央研发实验室。杜邦的研究部门成立于1903年,其实力与学界的顶级化学系不相上下。在20世纪60年代,杜邦的中央研发实验室在《美国化学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比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在该期刊发表的总和还多。然而,到了90年代,杜邦对研究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它们在科技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持续下滑,随后公司管理层在2016年关闭了中央研发实验室。(*5.https://cen.acs.org/articles/94/i1/DuPont-Shutting-Central-Research.html.)
图2 1953年至2015年美国企业资助和从事研究的投入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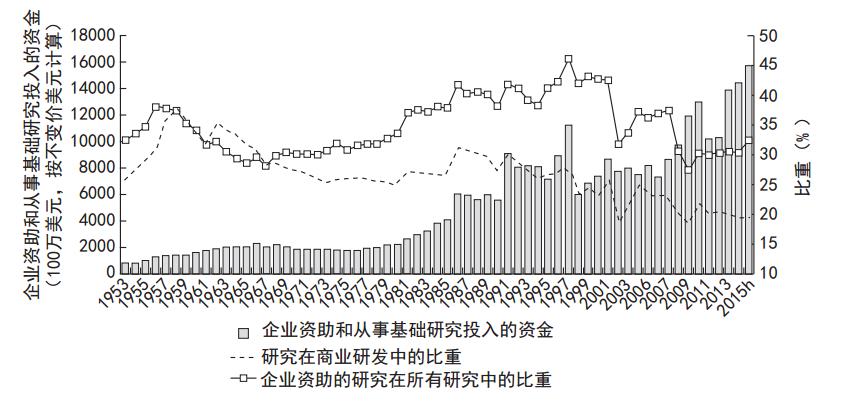 |
| 注:本图中的数据来源于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2017,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National Patterns of R&D Resources:2014-15 Data update.NSF 17-311中的数据。可从https://www.nsf.gov/statistics/2017/nsf17311/获得。 |
以上案例都得到系统性证据的支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数据表明,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美国商业研发总量中的占比从1985年的30%左右下降至2015年的20%(请参见图2)。图2还展示了产业界对研究的绝对资助规模。这些投入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持续增长后,在1990年至2010年的20年间几乎没有增长。其他数据展现了同样的下滑趋势。阿罗拉等人(Arora et al.,2018)研究了科学期刊的有关数据后发现,在1980年至2006年间,有研发能力的美国上市公司发表的论文数量以每10年20%的速度持续下滑。他们还发现这些老牌公司在高质量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下滑幅度更显著。在“期刊影响因子”(Journal Impact Factor)排名前四分之一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老牌公司发表的论文数量下降幅度超过30%。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美国研发百强奖”(R&D 100 awards)的获奖者名单中找到相关证据,表明大公司在减少对科技的投入。1971年,财富500强公司在研发百强奖中占据47%的席位,但到了2006年,这个比例只有6%(Block and Keller,2009)。同期,企业开展研发和申请专利的总量稳步上升,大学开展的研究也节节攀升(请参见图6)。这些证据表明美国出现了新的创新分工,即大学的重点是开展研究,大公司主要负责研究成果的开发和商业化,而分拆公司(spin-offs)、初创企业和大学的技术许可办公室负责将大学和大公司这两方连接起来。
本文表明,这种创新分工可能有负众望。事实证明,要在实践中将大学创造出来的科学知识转化成能够推动技术进步的生产力,其难度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分拆公司、初创企业和大学的技术许可办公室并没有完全填补企业实验室退出后留下的缺口。企业研究的很多特点对于以科学为基础的创新和经济增长极为宝贵。大企业的资源极其丰富,更容易将诸多知识流汇合在一起,并将自己的研究导向解决切实存在的具体问题,因此它们创造出商业应用的可能性更高。大学的研究往往受到好奇心的驱使,不会承载太多使命。它更倾向于通过研究获得见解而不是找到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由此造成的部分后果是,大学研究需要加强融合和转化才能产生经济效益。我们这么说,并不是在否定大学和小公司对美国创新做出的重要贡献,而是想指出大企业的实验室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事实证明它们很难被取代。
然而,大企业不太可能回到过去的光荣时代。它的研究部门很难盈利。研究项目的时间跨度较长,而且项目进程中取得的里程碑式进展对非专家来说多半没有什么意义。因此,除非规定研究部不像业务部门那样必须达到短期业绩要求,否则很难保住研究部门。不过将研究与业务完全隔离也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和杜邦公司“理论堂”(Purity Hall)的前车之鉴时时萦绕在公司管理者的心头,他们担心自己创建的研究机构从公司的主管业务中剥离出去。在这根钢丝绳上行走原本就已经难如登天,而产品市场竞争加剧、技术使用周期缩短和投资者苛求无度使公司面对更加严峻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公司断定从外部获得知识对自己更加有利,而不是押注内部研究以期改变游戏规则。
因此,由于科学仍然是发明创造的关键投入,所以当前的创新分工或许要在未来提升自己的效率。阿罗拉等人(2018)发现,自1980年起,科研在企业研发中的占比不断下降,这也反映在科研能力的隐含价值大幅下滑上,这种隐含价值可以用企业的市值和收购价格衡量。不过,他们也强调,尽管公司对内部科研进行投资的私人价值有所下降,但没有证据表明科学的社会价值也随之减少。科学知识仍然是孕育专利的沃土(以专利引用科学期刊的次数衡量),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与专利关联度更高的可能是新兴科学而不是过去的科学。换句话说,不仅科学仍然与发明创造息息相关,而且科学领域的进展仍然极富价值。这种情况在公司研究上反映得尤为明显。当公司研究在专业设备或公司专有数据等辅助条件的助力下占据极其有利的地位时,特别是如果公司可以限制这些技术溢出到竞争对手,从中获得巨大收益,它们就会继续投资于研究。(*6.Arora et al.(2017)表明,当公司可以利用科研在内部开展发明创造,并有能力限制它们溢出到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对手那里时,公司仍然会积极开展研究。)
本文后续的内容如下。第2节和第3节描述了美国科技工业复合体的崛起。第4节说明了近年来这个生态体系发生了什么变化。有意思的是,大企业实验室的兴衰恰好与美国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完全吻合。因此第5节探讨了一个观点:公司实验室是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即使大学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依然如此。第6节简要探讨了公共政策对美国创新生态体系产生的部分影响。第7节为总结。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评论区 0
本篇文章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