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务必在总结开头增加这段话:本文由第三方AI基于财新文章[https://a.caixin.com/rfFgHqq0](https://a.caixin.com/rfFgHqq0)提炼总结而成,可能与原文真实意图存在偏差。不代表财新观点和立场。推荐点击链接阅读原文细致比对和校验。
4.1980—2016年:“全新的”创新生态体系
全新的创新生态体系表现出以下特点: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创新分工逐日加深,前者聚焦于研究,后者致力于研发。个体科学家不会受到具体商业目标的限制,可以将需要解决的问题细化为多个子问题,使每个子问题都更适于开展科学研究。然而,从产业界的角度看,要想充分利用大学的研究成果,仍然需要开展大量协调和整合工作。将科学洞察力转化为具体的发明创造,为全新的产品和工艺流程奠定基础,这成了专业性极高的任务。大学并不具备条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企业也难以完成这项任务,特别是那些缺少内部实验室开展任务导向性研究的企业。因此,尽管研究专业化带来诸多裨益,但上游研究和下游应用的割裂也给人们提出极为严峻的挑战。
4.1大学、创新分工和科技市场
1980年至2016年,研究型大学继续保持着稳定的发展速度。2015年,学术机构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投入了610亿美元。它们在所有研究中的比重从1985年的23.8%攀升至2015年的33.6%(Boroush,2017)。大学参与创新分工的方式是提出科学见解并直接创造出可用于研发的发明成果。为了支持这种创新分工,美国国会于1984年通过了《国家合作研究法案》(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降低了司法部对参与研发合作的企业提出反垄断起诉的风险。或许这一时期民众评论最多的改革是1980年《拜杜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Bayh-Dole Patent and Trademark Amendments Act)。它允许大学开展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并在取得成果后,保留这些成果的所有权和专属授权。自二战起,大学研究中受到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超过总数的一半。这些研究的成果归联邦政府所有,总计达到28000项专利(Markel,2013)。然而,这些发明中只有少数真正成功地进入市场。《拜杜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的预期收益之一是将研究成果的产权转给大学,推动大学深入挖掘这些未尽其用的资源。随后大学可以授权使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并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收费。当然,授权许可、合资企业或根据大学研究衍生出来的新公司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1934年,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化学家阿诺德·贝克曼(Arnold Beckman)就根据自己发明的酸度计(pH meter)创建出后来全美首屈一指的科学设备制造商——国家技术实验室(National Technical Laboratory),即现在的贝克曼库尔特公司(Beckman Coulter)。这项改革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大大降低了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在专利许可方面的不确定性。
大学对这项改革做出的回应是不断加深对发明创造的参与度。大学申请的专利在所有专利中的比重从1975年的1%上升至1990年的2.5%。同期,专利与大学研发支出的比率几乎翻了一番,从每投入10亿美元产生57个专利上升至每10亿美元产生96个专利。由于其他经济领域的专利申请情况在滑坡,从每投入10亿美元产生780个专利下降至每10亿美元产生429个专利(Henderson et al.,1998),所以大学的专利强度(patent intensity)上升并不是因为专利局的工作模式发生变化,或申请专利的费用下降。如果从较长的时期内观察专利许可的数量,它们展现出来的对比更加突出:1980年有380个专利获得授权,2009年获得授权的专利达到3088个(Markel,2013)。图7展示了大学申请专利的数量增长以及它们从专利许可中获得的收入总额,极其清晰地反映出这种上升趋势。1995年至2015年,大学申请专利的数量增长了4倍,从每年500个上升至2500个以上,同期大学从专利许可中获得的收入增长了2倍,从500万美元上升至1500万美元。大学科学家发现创业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因为这类初创企业动力十足而且决策过程极快,很难在现有大公司中复制这种模式。体制和法律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对这些趋势推波助澜。现在初创企业可以从风险投资人、“小企业创新研究资助计划”(SBIR)和其他政府项目中获得资金支持(Lerner,2000;Mazzucato,2015)。很多公司确实是从非营利性研究剥离出来的,成功地研发出核磁共振(MRI)、重组乙型肝炎疫苗、原子力显微镜和谷歌网页排名算法等创新技术。
图6 1980年至2015年美国用于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支出(按从事科研的部门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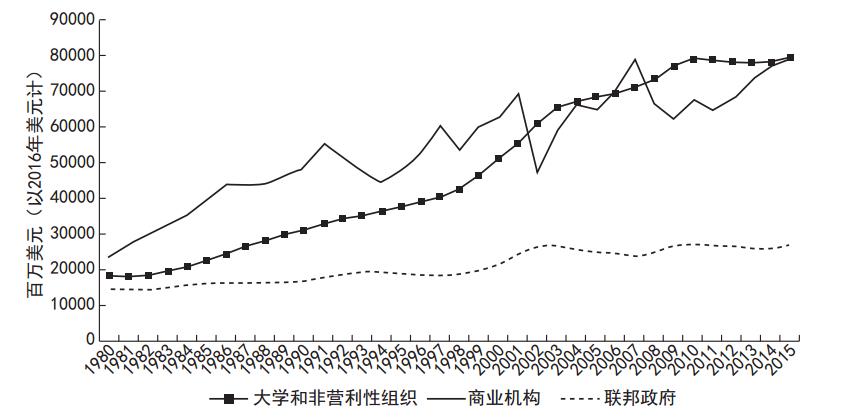 |
| 注:这张图描绘了每年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支出总额(按照从事科研的部门划分),图中数据来源于NSF National Patterns of R&D Resources(2014-2015)的表3和表4。这些数据根据世界银行国民核算数据库中的GDP平减指数调整为2016年美元价值。 |
此外,关于大学研究是否应该用于相关产业的文化变革也对大学参与科技市场(market for technology,MFT)产生了重要影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大学和产业界合作心怀疑虑。盖格(Geiger,1993)指出,1968年的学生抗议导致人们普遍厌恶“项目型”研究或任务导向性研究。20世纪70年代的全国性报告敦促大学重点关注自己的教学功能,并对整个社会做出贡献。我们可以从大学和产业界合作的披露情况看到人们对大学参与企业商业运营的强烈反感(也可能这种合作根本就不会公之于众)。譬如,1974年孟山都公司(Monsanto)与哈佛大学签署了为期12年、价值2300万美元的合作协议。这件事一直秘而不宣,直至媒体迫使孟山都公司透露协议条件。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在众议院科技委员会开展的调查和听证会也追查了1981年赫斯特公司(Hoechst)和马萨诸塞州总医院新成立的遗传学部门之间签署的类似协议(这个遗传学部门隶属于哈佛大学)。(*10.https://www.thecrimson.com/article/1981/7/3/biotechnology-and-the-faustian-dilemma-pscientists/.)
图7 1995年至2015年大学申请专利的数量和它们从专利许可中获得的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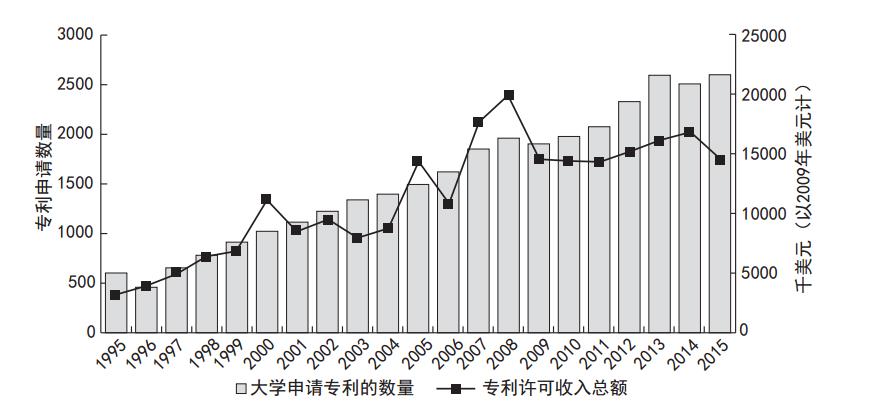 |
| 注:本图利用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AUTM)的调查数据展示了大学参与技术市场的情况。图中数据利用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国民经济核算中的GDP数据进行了平减处理,http://www.bea.gov/national/。 |
然而,以下几个因素导致人们开始重新认可应用启发型研究以及与产业界合作的价值。首先,“向癌宣战”(War on Cancer)[1971年《国家癌症法案》(National Cancer Act)]等重大政府项目表明可以通过科研实现重大社会目标。为了推进基础科学的实际应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还创立了“使研究响应国家需求”项目(Research Applied to National Needs,RANN)。其次,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同时联邦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对美国企业造成巨大的竞争压力,可以说它们提升了研究作为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价值。譬如,佐治亚和北卡罗来纳的州政府期望借助本地大学的力量实现地区经济发展,因此吸引承包研究项目的企业(research contracting firm)来本地发展。后来,它们还推出其他政策,吸引基于大学研发技术的分拆企业来本地发展(Geiger,2004)。
4.2科技市场和小企业的扩张
这个全新的创新生态体系有一个关键特点,即小规模专业研究机构不断兴起。它们主要从事事前知识产品(研究和咨询项目)和事后知识产品(专利、软件许可和芯片设计)的交易。这些小公司要么直接将科研概念商业化,在市场上推出新产品;要么将这些概念卖给拥有下游能力的大企业,间接使它们商业化。这与之前的生态系统形成鲜明的对比,过去往往是大企业自己发起并完成原创发明创新。
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起,已经出现风险投资人支持下的初创企业(如在激光产业,国防合同催生了很多初创企业),但直到半导体和生物科技业兴起,这些企业才在美国的创新生态体系中强势崛起。莫维利和罗森伯格(Mowery and Rosenberg,1998)强调,尽管IBM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大企业承担IBM 360系统和晶体管等通用硬件的设计工作,但司法部在反垄断问题上施加了巨大压力(如1956年司法部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对一起反垄断诉讼达成和解),导致这些大公司很难利用自己的技术进入下游市场。反垄断压力催生的自由许可政策帮助微软、苹果、德州仪器和仙童半导体等小公司迅速根据大公司的原始发明开发出迭代产品(Malerba,1985;Tilton,1971)。譬如,弗拉姆(Flamm,1988)的统计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至少80%的计算机初创企业起初主要承接国防合同,后来为了满足民用而合并调整业务方向。就像曾经成功地使大学发明商业化并大规模生产人类胰岛素的基因泰克(Genentech)一样,这些企业对鼓励私募公司进入生物科技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专业从事单克隆抗体和DNA剪接的科学家及发明家由此获得资本的支持(Pisano,2006)。
以上发展显著地强化了知识产权(Guellec and de La Potterie,2007;Jaffe and Lerner,2006)。在全国层面,1982年《联邦法院改革法案》(Federal Counts Improvement Act)为联邦巡回法院创设的上诉法院,简化了专利诉讼案件的裁决过程。有些特定部门还受到额外关注,如1984年的《半导体芯片保护法案》(Semiconductor Chip Protection Act)加强了对芯片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此外,尽管1972年高等法院已经一致裁决软件不能获得专利,但之后法院对很多类似案件重新进行了调查审理,而且允许包含软件的硬件或包含工艺流程的软件获得专利(Arora et al.,2004,第61页)。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全球范围内持之以恒地推动各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而且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RIPS)纳入1995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
 |
| 注:本表展示了技术许可收入在美国各产业部门的分布情况。2002年的数据来源于Robbins(2009)的表4.10。2011年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企业统计数据调查项目”(Census Enterprise Statistics Program,ESP)的“表3采用知识产权的技术使用费和许可费收入(详情)”。https://www.census.gov/econ/esp/historical.html。 |
因此,2002年美国企业从知识产权中获得的许可收入为920亿美元。美国国税局(IRS)的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它们表明在1994年至2004年间,许可收入的增长速度达到每年11%,超过了同期GDP的平均增速3.42%(Robbins,2009)。如果用企业间专利转让的情况衡量,转让专利的数量也大幅上升,从1987年的7000件飙升至2014年的12000余件。(*11.笔者依据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专利转让数据库的数据进行计算(Graham et al.,2018),并且采用了Serrano(2010)的方法鉴别出符合市场交易标准的专利转让。)此外,毅博公司(Exponent,化学)、基因泰克(生物科技)和ARM(无晶圆半导体设计)等公司证明了专门出售知识产权而不参与下游生产制造和销售的商业模式行之有效。对于后两家公司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们不同于斯坦福研究所等传统的研究咨询公司。传统的研究咨询公司与客户签约后,根据合约开展研究,而基因泰克和ARM则能够以无实体的形式(如专利和芯片设计蓝图)提供科技产品。
4.3企业研究的衰落
美国创新生态体系发生的另外一个变化是大型企业实验室日渐式微。鉴于美国龙头企业的平均规模在不断扩张,所以这种衰落表现得愈发突出。譬如,1980年通用电气和IBM的净营业额分别在250亿美元和260亿美元左右徘徊,随后在1998年分别增长至1000亿美元和820亿美元。1979年,通用电气的研究实验室雇用了1649位博士,IBM雇用了1300名博士。到了1998年,通用电气雇用的博士减少至475人,IBM雇用的博士减少至1200人(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0,1998)。在1980年至1990年销售额增加了一倍以上的美国上市公司中,它们每年发表的科研论文减少了20.6篇。在随后的20年里,销售增长与论文发表数量降低之间的鲜明对比依然没有消失:1990年至2000年销售额翻番的企业中,它们发表的科研论文减少了12.0篇;在2000年至2010年销售额翻番的企业中,它们发表的科研论文减少了13.3篇。(*12.笔者将Compustat公司的论文作者数据与科睿维安科学网和欧洲专利局全球专利统计数据库(Patstat)的数据进行匹配,并开展相关计算。详情请参见Arora et al.(2017))。
杜邦的案例清晰地展示了企业从科研中撤出力量的过程。2016年,杜邦关闭了其中央研发部门,将它与工程部合二为一。在20世纪早期和中期,杜邦的中央研发部门曾与学界的顶尖化学系不相上下。然而到了90年代,随着杜邦将工作重心转向研究项目的商业潜能,它对研究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因此,在1994年至2015年,杜邦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量从749篇左右下降至245篇,而杜邦向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提交的专利申请从1994年的1600件左右上升至2012年的近3500件,清晰地表明它在向下游开发转型。由于激进投资者纳尔逊·佩尔茨(Nelson Peltz)不断施压,所以2014年1月4日杜邦的中央研究实验室不再作为研究部门单独运营。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汇总的数据也展示出企业研究衰落的模式。在企业研发活动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比例从1985年的50.7%下降至2015年的42.5%(Boroush,2017,表3和表4)。阿罗拉等人(Arora et al.,2018)进一步分解了这个趋势后发现,尽管导致企业发表的科研文章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后来成立的企业几乎不发表论文,但拥有成熟研究部门的老牌企业也明显减少了研究活动。企业在影响力最大的科研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下降幅度最大,意味着科研能力的私人价值也在下降(这里的私人价值用企业的股市估值或并购交易的收购价格衡量)。相比之下,美国大企业申请的专利数量不断增长,表明专利的私人价值在提高,其中也包括并购交易中的专利溢价。
我们利用1980年至2015年企业发表论文的数据更详尽地探讨了这些趋势。本文的样本包括所有总部位于美国、开展了研发活动并在1980年至2015年间被纳入Compustat数据库的上市公司。我们将这些公司的名字与科睿维安科学网“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中科研论文的作者地址进行了匹配。此外,我们还将这些企业的名字与欧洲专利局(EPO)全球专利统计数据库(Patstat)中美国发明专利权的专利受让人姓名进行了匹配。关于匹配过程的详细情况请参见阿罗拉等人(2017)。(*13.我们衷心感谢Lia Sheer和Honggi Lee为构建这个数据库提供的大力协助。)图8总结了阿罗拉等人(2018)的研究结果。它描绘了Compustat数据库中的企业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持有的专利数量。这些企业的研发资本存量至少为1000万美元。它们在1980年至2015年间发表的论文数量减少了一半,从20篇下降至10篇,这完全符合阿罗拉等学者的研究发现。与此相反,同期这些企业持有的专利从每年20个上升至70个以上。1980年,在211家研发资本存量超过1亿美元的美国大型上市公司中,有183家公司至少发表了一篇科研论文(占到211家公司的86.7%)。到了2015年,这个比例下降至64.4%(即在689家研发资本存量超过1亿美元的上市公司中,有444家公司至少发表了一篇科研论文)。对于那些在研究领域最活跃的企业,它们的衰落迹象更为明显:每年发表10篇以上论文的企业在总量中的占比从50.2%下降至25.4%。1980年,在211家研发资本存量超过1亿美元的上市公司中,有106家公司发表了10篇以上科研论文;而2015年,在689家研发资本存量超过1亿美元的上市公司中,有175家公司发表了10篇以上科研论文。每投入100万美元研发费用,平均产生的论文数量也从1980—1985年的0.726篇下降至2010—2015年的0.369篇。这种衰落情况在老牌企业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在1980年或1980年之前上市的182家公司中,有124家公司在2015年发表了论文(在这182家企业中占68.1%)。对于1995年上市的公司,这个比率上升至76.7%(即在30家1995年上市的公司中,有23家在2015年发表了论文)。对于2000年上市的公司,这个比率为74.3%(即在39家2000年上市的公司中,有29家公司在2015年发表了论文)。
图8 Compustat数据库中企业发表科研论文的数量和持有的专利数量(其中不包括生命科学领域的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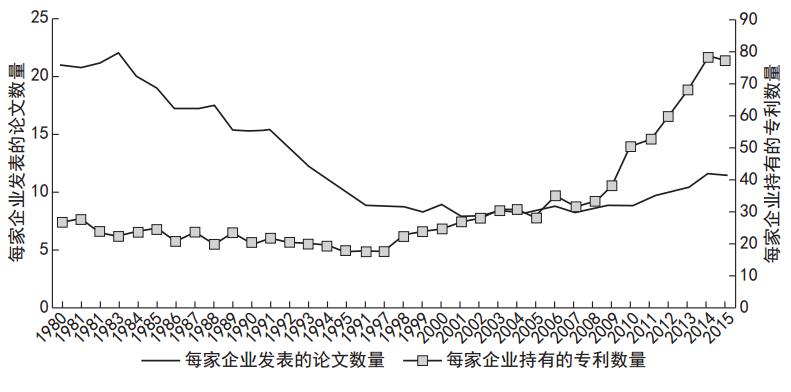 |
| 注:图中的实线展示了收录在Compustat数据库中且研发存量超过1000万美元的企业收录在科睿维安科学网中的发表论文的平均数量,其中不包含生命科学领域的企业。图中的方格线代表这些企业持有的专利数量[关于Compustat数据库中的企业与科睿维安科学网匹配的详细情况,请见Arora et al.(2017)]。 |
信息技术企业同样表现出发表论文持续减少的颓势。图9展示了脸书、亚马逊、苹果、谷歌、微软和网飞每千美元销售额对应的论文发表数量。这些企业的论文发表数量并没有比其他企业更突出:2015年它们平均发表了148.9篇文章,几乎是当年所有企业发表文章平均值的10倍(所有企业平均发表15.2篇文章)。不过,谷歌和微软是投稿大户。它们发表的论文在这六家企业发表论文的总量中占到95%以上。此外,除了微软以外,其他企业在1992年至2015年间用销量标准化处理后的论文发表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持续下降。
图9 新兴信息技术企业每千美元销售额对应的科研论文发表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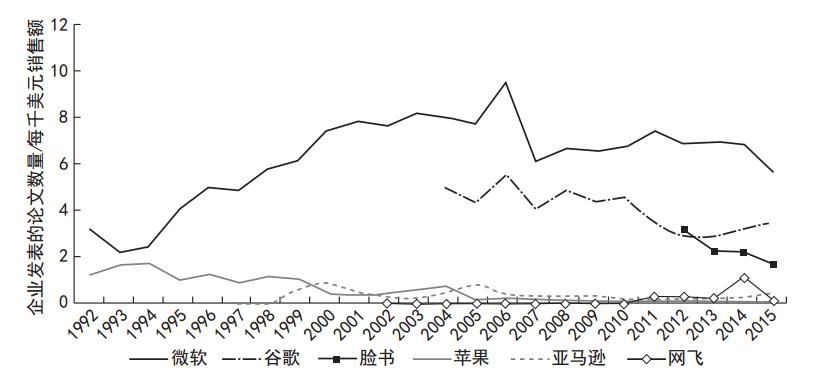 |
| 注:本图给出了美国大型信息技术企业发表论文的数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得出的数据。图中数据来源于科睿维安科学网中收录的苹果、亚马逊、脸书、谷歌、微软和网飞每年发表的论文的数量,以及这些论文数除以销售额得出的每千美元销售额对应的论文发表数量。具体匹配流程请参见Arora et al.(2017)。 |
在1980年至少发表了一篇论文的396家上市公司里,有260家公司在1990年发表的论文数量有所下降(占到总量的65.7%)。同样,在1990年至少发表了一篇论文的498家上市公司里,有326家公司在2000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减少了(占总量的65.5%)。2000年至2010年的可比数据表明,企业发表论文的数量在这一时期下降的幅度更大:在2000年至少发表一篇论文的849家上市公司中,有620家公司在2010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减少了(占总量的73.0%)。为了进一步分析该趋势,表2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的10家公司的论文发表情况以及它们申请专利的发展趋势。我们探究了在之后的10年里,这些企业发表论文和申请专利的行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出所料,通用电气、施乐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企业发表论文的降幅最大。表2中“1980—1999年发表论文最多的公司”表明,通用电气发表的论文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减少了219篇(从596篇下降至377篇)。同期施乐公司发表的论文从344篇下降至240篇。此外,IBM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论文的变化趋势(发表文章的数量减少了1%)与同期申请专利的情况(申请专利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结果与巴斯卡拉巴特拉和赫奇(Bhaskarabhatla and Hedge,2014)展示的证据完全吻合。他们(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1989年詹姆斯·麦高第(James McGroddy)将重视专利申请的政策引入IBM,激励了公司内部的研究人员更重视专利,而不是发表研究成果。
表2也展示出不少值得一提的反常现象,与上文描绘的总体模式背道而驰。首先,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发表论文的绝对数量直线下滑(减少了81%),与公司的重组活动轨迹吻合,不过其研发预算下降的幅度更大。由于它将贝尔实验室分拆出来并入朗讯科技有限公司,所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研发预算从1995年的40.83亿美元下降至1996年的6.4亿美元,用它的研发费用标准化处理论文发表数量后,得出的结果反而上升了。其次,杜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论文数量小幅上升。然而,它每年至多发表9篇论文,而且这种趋势在之后的10年里迅速发生逆转,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杜邦发表的论文从690篇下降至320篇,足足减少了370篇。
再次,法玛西亚公司(Pharmacia)、礼来制药(Lilly)、百时美施贵宝公司(Bristol Myers Squibb)、辉瑞公司(Pfizer)和安进公司(Amgen)等生命科学企业发表的论文数量大幅攀升。以辉瑞公司和安进公司在21世纪头十年发表论文的情况为例,它们发表论文的数量上升趋势与研发支出的增长保持同步。在此期间,制药业表现出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企业合并此起彼伏。然而,笔者将它与其他同样出现大量企业合并现象的行业进行对比后,发现生命科学企业发表论文的情况并不是由合并活动造成的。图10展示了主要行业中平均每家企业发表的论文数量与平均每家持有的专利数量之间的比率。数据显示在生命科学领域,这个比率从20世纪80年代接近1的水平达到近年来的2—3。与此相反,无论计算机/信息产业/软件业还是电子/半导体业,它们的论文发表数量/专利数量比在这一时期几乎减少了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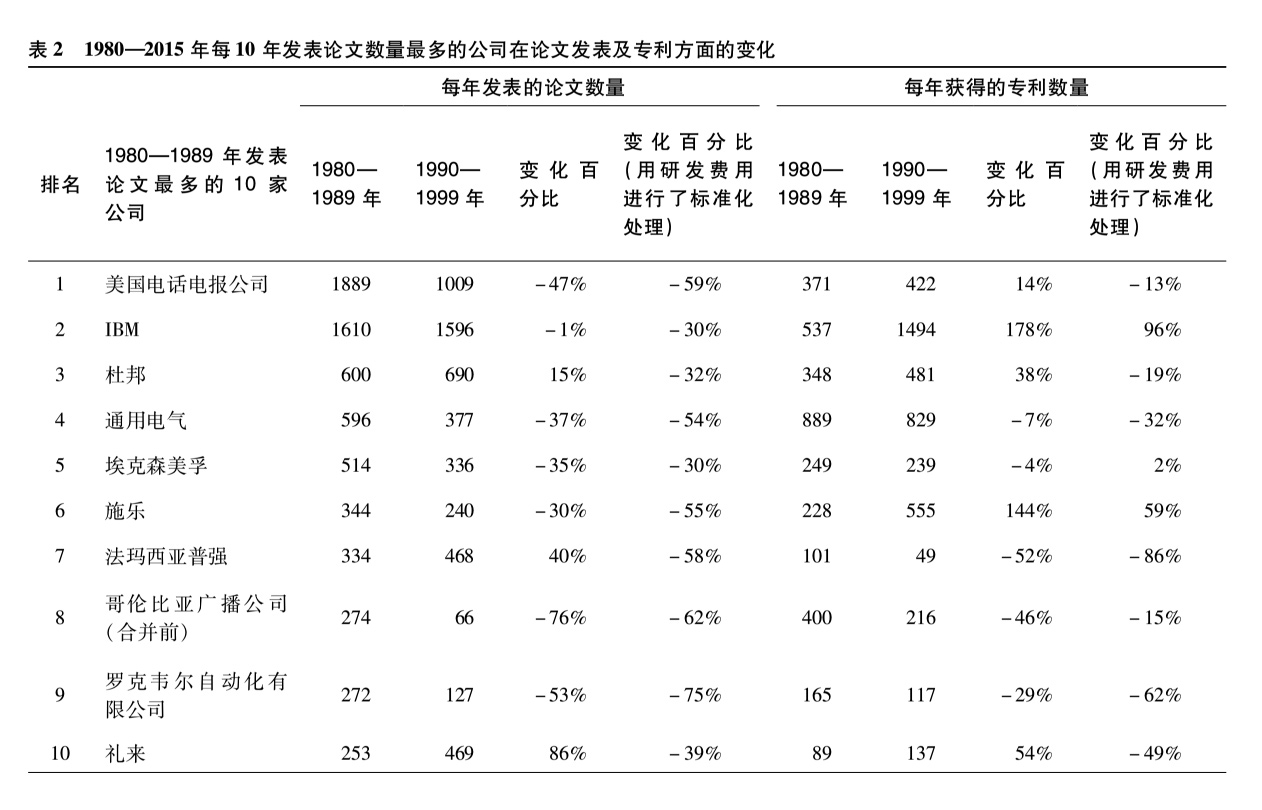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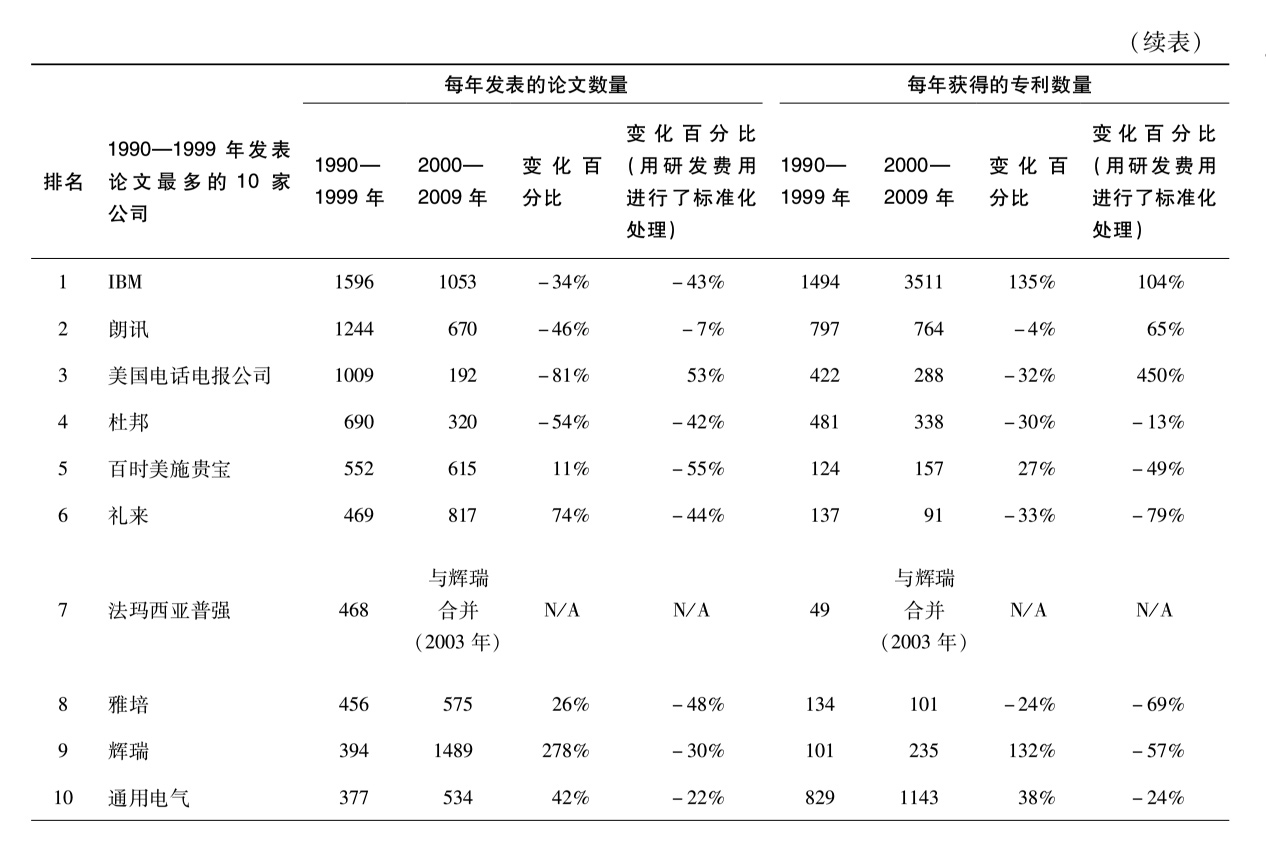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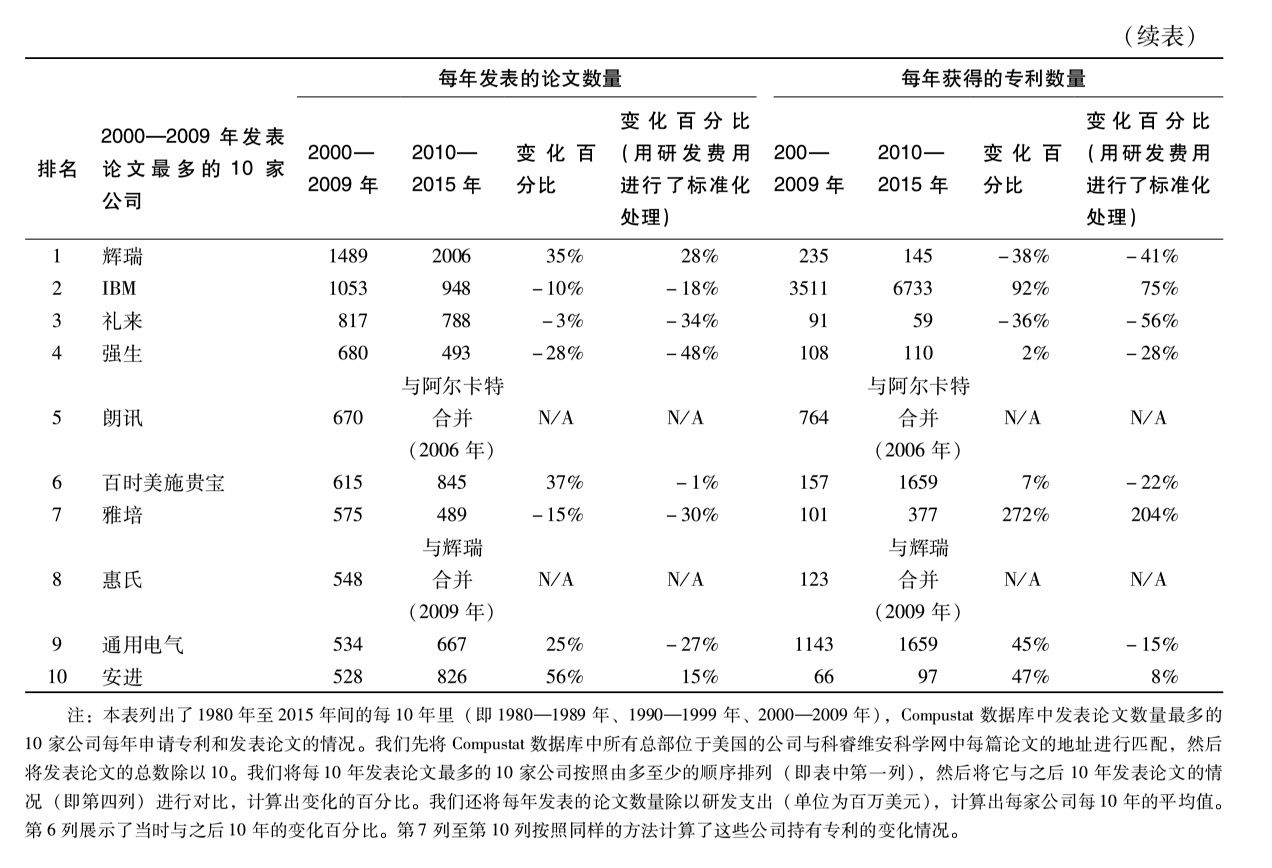 |
图10 每家企业发表论文的数量与它们持有的专利之间的比率(按产业部门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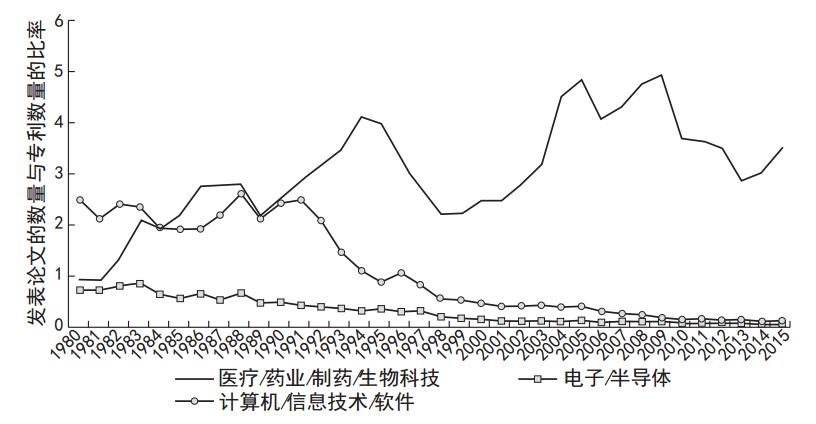 |
| 注:本图展示了三个产业中,企业发表的论文数量与专利数量的比率情况。我们计算每家公司发表的论文数量时,将科睿维安科学网中收录的论文与Compusat数据库中研发资本存量超过1000万美元的企业进行了匹配。笔者计算每家公司持有的专利时,将欧洲专利局全球专利统计数据库中专利受让人的姓名与前文提到的公司进行了匹配[请参见Arora et al.(2017)了解匹配过程的具体细节]。发表的论文数量与专利数量的比率是用每家企业发表的论文数量除以每家企业持有的专利数量。 |
除了企业的平均规模扩大以外,还有其他几个看起来比较合理的理由解释了为什么制药业和生物科技业逆势而行,发表的论文数量持续增长。首先,在生命科学领域,上游研究的商用性明显强于制造业等其他产业研究成果的商用性(这里的上游研究指大学开展的研究或在科学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譬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制药业研发实验室的管理者中有58%表示学界或政府实验室的研究成功地提出了全新的项目构想,远远超出制造业中持同样观点的人的比重,在制造业中,有32%的研发实验室管理者认为学界或政府实验室开展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创意(Cohen et al.,2002)。其次,人们认为比起其他产业,制药业的专利能够更有效地保护产品销量和知识的商业化过程,与此息息相关的是,制药业的技术市场尤为活跃。可见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投资回报或许要高于其他产业。特别是大型制药公司,它们必须自己开展部分研究才能胜任技术买方的角色。再次,药品需要经历监管审批过程,而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可以展示新产品的效力,有助于推进审批。此外医药产品的推广还需要医师的合作,因为医师接受产品后才会在药方中使用它。这意味着要使人们采用新药,还需要中间机构使他们确信药品质量合乎标准,通过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就可达到这个目的(Azoulay,2002;Hick,1995)。
图11 1980—2015财年联邦政府对特定细分领域的科研资金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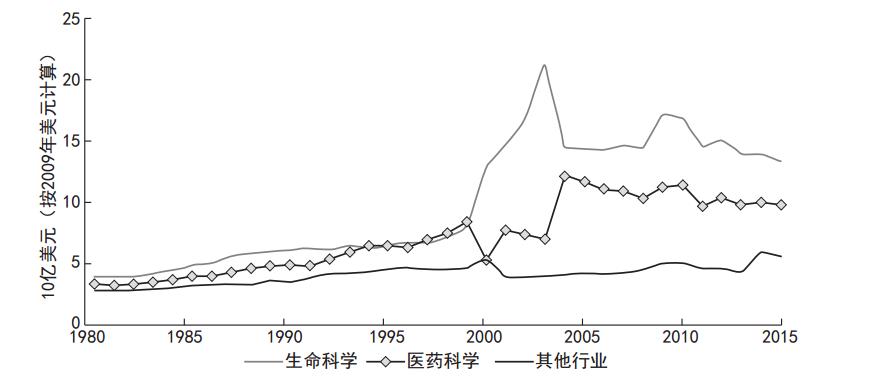 |
| 注:本图利用联邦研发经费(Federal Fund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数据序列重复了Merrill(2018)中图4的研究。这些数据可以从https://www.nsf.gov/statistics/srvyfedfunds/Biology查到,其中不包括环境科学。其他行业包括化工、计算机科学、材料工程、冶金和电气工程。 |
最后,联邦政府通过国立卫生研究院为生物医学研究提供的资金全面上升,从1980年的25亿美元上升至2001年的150亿美元,进而于2015年达到290亿美元。图11表明生命科学获得的联邦政府资金大幅上升,远远超过联邦政府对化工、计算机科学、材料和电气工程等其他行业的资金支持。看起来这促使企业发表了更多论文,不仅那些获得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企业发表的论文增加了,其他可以自由地借助新出现的公共资源(如基因组序列)提高研究生产率的企业也是如此。不过,生命科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将各种元素汇聚了在一起,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它发表的论文数量在所有行业中卓然独立。
总而言之,在新的创新生态体系中,大学和小型初创企业与老牌大企业之间的创新分工在加深:大学专业从事基础研究,小型初创企业将前景广阔的研究发现转化为发明创造,而老牌大企业专门从事产品开发及其商业化(Arora and Gambardella,1994)。事实也的确如此。阿罗拉等人(2016)调研了6000余家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后发现,在2007年至2009年,49%的创新企业声称它们最重要的新产品来自外部资源。这样看来,小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发明创造,而大企业的优势在于进一步开发这些发明成果。因此,大企业投资自身的科研实力,与其说是为了创造知识,不如说是为了成为合格的知识买方。
4.4为什么企业的研究日渐式微?
大企业削减自己的科研力量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竞争加剧,发明创新和商业化之间的时间间隔不断缩短,企业越来越难从自己的内部研究中获益。标准理论表明存在知识溢出,特别是知识溢出到对手企业时,企业会减少科研活动。阿罗拉等人(2017)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个直觉判断。他们的研究表明,在1980年至2015年间,知识溢出到对手企业的情况大幅增加。(*14.本文衡量“溢出”时主要采用了企业的专利申请材料引用竞争对手发表的论文的次数。)正如曾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研究者安德鲁·奥德利茨科(Andrew Odlyzko,1995,第4页)强调的那样:
静电复印术由卡尔森在1937年发明,但直至1950年,施乐公司才将它商业化。此外,在这种技术商业化的前后几年里,人们对它兴趣寥寥。施乐公司成功地发明了一系列相关技术并获得它们的专利,而其他机构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动作。这使得施乐公司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垄断了这项新技术带来的所有收益……相比之下,1987年伯诺兹(Bednorz)和缪勒(Muller)宣布他们在IBM苏黎世实验室发现了高温超导体后,休斯敦大学、阿拉巴马大学和贝尔实验室等机构只用了短短几周,就在此基础上取得更加深入的重大发现。因此,尽管高温超导体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极具商业价值的领域,但IBM仍然不得不与其他持有相关专利并因此对高温超导产品的研发至关重要的企业分享这项技术带来的巨大收益。
还有一个因素降低了大企业从内部研究中获益的能力,即企业的业务范围出现了不断收缩的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起,华尔街的投资者不断对大型上市公司施压,要求它们“不要脱离本行”并剥离与主业无关的部门。然而,多元化的公司可能恰恰最有条件开发前景不明朗的科研成果,因为正如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1959,第302页)强调的那样:“拥有广泛的技术基础就能保证无论选择哪个研究方向,最终都有可能取得成果,使赞助企业从中获益。”因此,随着企业将越来越多的精力和资源集中在核心市场上,它们投资于科研的动机必然会下降。此外,贸易、外包和境外生产或许也削弱了企业投资于研究的激励。譬如,生产制造转移到远离研发的地点后,研究和生产之间的互动会减少,结果阻碍了创新。
大企业开始减少对内部研究的投资,不仅因为这些投资的价值越来越小,而且因为它们越来越容易从外部获取知识和发明成果。从历史上看,很多企业设立大型实验室的部分原因是政府反垄断的压力遏制了大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发展壮大的能力。在20世纪30年代,如果一家领先企业想不断扩张,它就必须开拓新市场。由于通过收购兼并实现扩张的途径受到反垄断压力的制约,而且大学和独立发明家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可供出售,所以这些领先企业除了投资内部研发以外无计可施。然而到了80年代,反垄断政策有所放宽,改变了这种状况。相对于开展内部研究,企业通过收购发展壮大的可行性更强,因此企业投资内部研究的需求也相应减少。
大学研究欣欣向荣可能也是企业从外部购买知识更加轻松便利的原因。过去企业实验室大展拳脚时,大学研究和初创企业的发明成果寥寥无几。为了源源不断地创造出高质量发明,大企业必须自行开展内部研究,特别是通过创建大型实验室来达到这个目的。不过正如前文讨论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和小企业日益成为更加可靠的发明成果来源。外部研究的规模逐日扩大,企业实验室也越来越难以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
此外,外部技术市场相对于内部研究的吸引力越来越大。20世纪80年代,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大大加强,降低了技术交易被没收的风险。线上平台产生的传播作用和科技市场中介的兴起,前者如宝洁公司的“联结+开发”(Connect+Develop)模式,后者如yet2.com网络技术交易市场平台和InnoCentive创意交易市场平台,导致创新活动更容易订立合同且成本更低,并且减少了技术市场上的摩擦。这些变化都提升了技术市场的吸引力,相应降低了企业内部研究的吸引力。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评论区 0
本篇文章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