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务必在总结开头增加这段话:本文由第三方AI基于财新文章[https://a.caixin.com/iJfX77ty](https://a.caixin.com/iJfX77ty)提炼总结而成,可能与原文真实意图存在偏差。不代表财新观点和立场。推荐点击链接阅读原文细致比对和校验。
区域间移民主要受房价影响吗?
主流理论用美国东南部和西南部较宽松的住房管制来解释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Glaeser,2008;Graves,1983;Roback,1982)。大多数此类模型进一步假设“工作随人走”,以此假定住房和便利设施在偏好函数中排名很高(Muth,1971)。他们的典型例子是战后美国阳光地带的发展,其中涉及大量的国内移民(南部地区从农村到城市;中西部/东北部工业地区到南部和西部)。但是,在此类文献中,这些移民潮是由发展中区域廉价住房推动的假设缺乏历史证据。
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这种迁移是东北部和中西部心脏地带常规制造业解体释放出来的,再加上20世纪40年代《国家劳工关系法案》的“塔夫特-哈特利修正案”对就业市场放宽管制,由此导致在奉行“自由工作权”的州组织工会更加困难。这延长了战后乡村-城市转型中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期限。因此,这些地区的增长应归功于工作的转换,这是由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而非不受管制的住房市场推动的。相比之下,向加利福尼亚州的大规模移民显然不是因为廉价住房,因为在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城市房价均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
随着制造业经历了向南迁移、技术变革以及全球化三个阶段的解聚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的失业率迅速增加,这就是俗称的“就业的新地理学”和“大反转”(Moretti,2012),于是就业作为城市增长和衰退之关键因素的观点逐渐深入人心。导致这些城市和地区人口减少的不是高度管制的房地产市场,而是就业人数的下降。后来,随着新经济的到来,尽管住房受到严格管制,但波士顿、华盛顿和纽约(以及英国伦敦)等旧经济的某些特定部分脱胎换骨,扭转了人口下降的趋势。
这两个人口变迁案例的区别在于工作的类型和产生这些工作的产业成熟度(Norton and Rees,1979)。在迅速发展的美国阳光地带城市中,几十年来平均技能和工资水平一直低于华盛顿、西雅图和旧金山等城市。决定高成本地区(如纽约或旧金山)与低成本地区(如奥兰多或菲尼克斯)日益扩大的房价差距的一种力量是那些寻求住房的人在工资和财富方面的差异(Romem,2018)。因此,房价差异并不是由移民水平(总需求)唯一决定的,也取决于移民结构。此处的“结构”是指人口的工资和收入结构。如果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只需常规技能且工资适中的就业驱动,其房价就会低于那些吸引了高技能、高薪人群的大都市地区。一个例外情况是总需求疲软,这解释了为什么锈带的大多数中型城市(布法罗、密尔沃基、南本德、锡拉丘兹)的住房价格很便宜,住房成本很低,人们还是离开了。罪魁祸首是缺乏工作岗位和机会。相比之下,在增长中的阳光地带城市,就业增长主要发生在中低薪行业。正如奥托(Autor,2019)所说,这一趋势如此之强,以至于“低技能工人密集的城市正在丧失其经济优势”。1950年,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不仅为受过良好教育、也为受过较低教育的工人提供了更高的工资。如今,当根据(人口)密度调整工资时,没有大学学历的工人从大城市中可获得的好处很少。欧洲也发现了类似的趋势。比耶克和梅兰德(Bjerke and Mellander,2019)发现,从瑞典的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地区,对迁移者的工资没有积极影响,只有高技能者例外。尽管人口稠密地区的住房成本加重了低技能工人的劣势,无论如何,降低住房成本都无法消除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劳动力市场的上述基本事实,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的,这些基本事实源于经济地理的根本性变化。
住房文献中的最新一代模型集中在就业地理上。高柏(Gaubert,2018)认为,企业的分类和住房紧密相关。在她的模型中,当今的城市规模偏小,因为公司无法从潜在的集聚经济中获得提高工人生产率的所有潜在收益。她认为,大城市的工资因住房管制导致的住房成本过高而膨胀。因此,如果增加住房供给,将拉平区域间的工资曲线,吸引更多的公司进入大城市,并因此内生出更多的集聚外部性。其中的关键机制是增加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形成更大、更高产和更专业化的城市。该模型肯定了我们的观点,即无论是由住房供给增加还是其他因素引起的城市增长,基本上都会使技能工人享受较高的城市工资溢价(Autor,2019; Bjerke and Mellander,2019)。图4形象地呈现了住房价格变化、已开发居住区的扩展和美国城市移民之间的弱相关,这支持了我们的观点:起作用的更多的是经济地理学的基本因素而非房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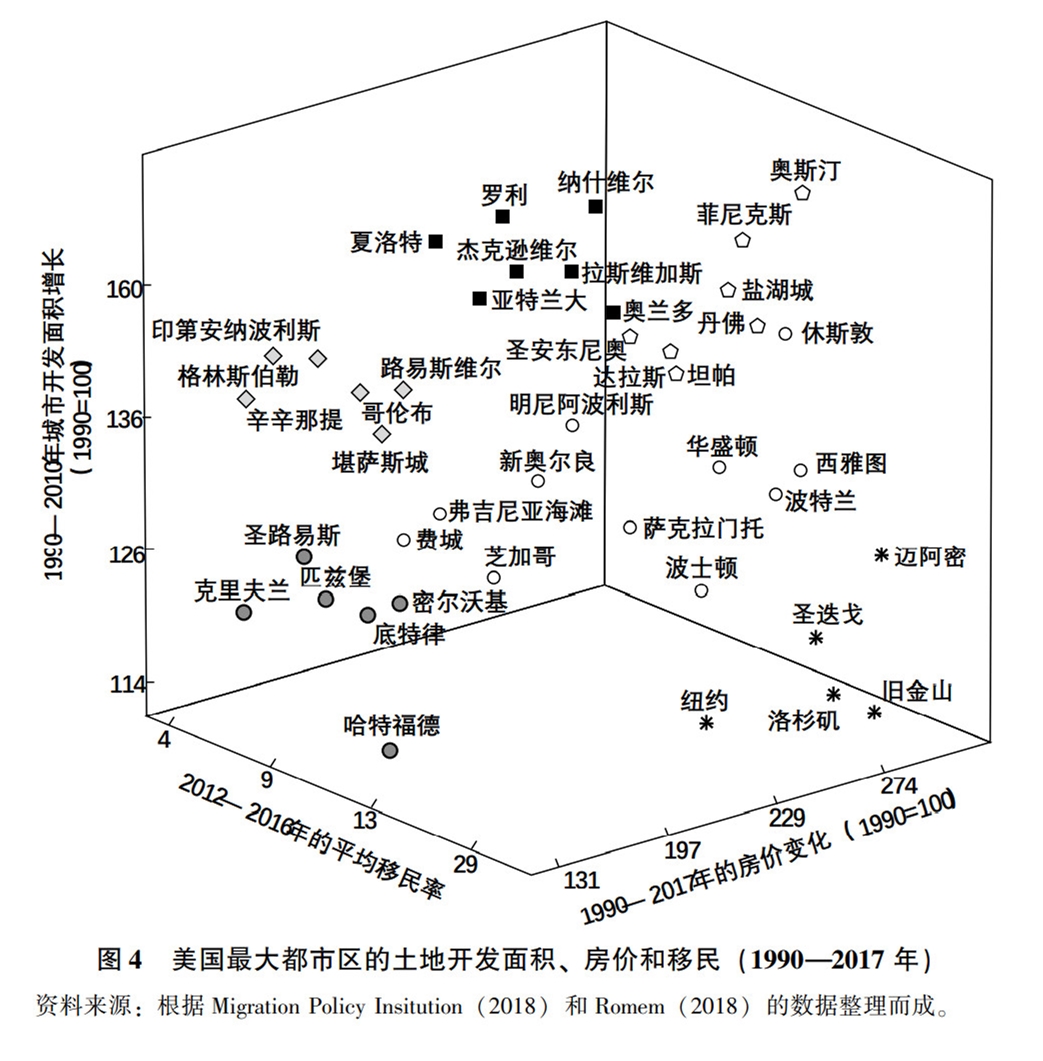 |
图4美国最大都市区的土地开发面积、房价和移民(1990—2017年)资料来源:根据Migration Policy Insitution(2018)和Romem(2018)的数据整理而成。“住房即机遇”学派的文献强调的住房扩张与低价住房升值之间的关系仅出现在少数南方城市中,如图4中的黑色正方形所示。在1990—2010年,夏洛特、罗利、纳什维尔、亚特兰大,杰克逊维尔、拉斯维加斯和奥兰多的土地开发面积迅速增长确实伴随着房价的适度上涨。但是,可负担的住房几乎没有吸引移民,因为与美国其他城市相比,这些城市中来自美国以外的移民数量仍然很少。总体而言,这些城市是异常值,而不是常规值。
实际上,常规值并不存在,这表明除了住房管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住房扩张、可负担性、流动性和城市增长之间的关系。许多具有严格分区和房价强劲上涨的城市(图4中用星号标示的城市)继续吸引着人口和大量移民。迈阿密近40%的人口为外国移民,在大城市中排名第一。洛杉矶名列第二;旧金山排名第五;圣迭戈和纽约紧随其后。另一组美国城市(图4中用小菱形标示)包括印第安纳波利斯、辛辛那提、格林斯伯勒、哥伦布、路易斯维尔和堪萨斯城,住房增长迅速的同时房价保持低位,但未能吸引移民。在其他大城市中,奥斯汀、菲尼克斯、盐湖城、丹佛、达拉斯、圣安东尼奥和坦帕(图4中用小五边形标示),住房的快速增长并未带来更好的可负担性。尽管这些城市的移民比例比拥有更多可负担住房的区域更高,但吸引的移民规模却落后于住房存量几乎没有增长的较昂贵区域(图4中用星号标示)。最终,像克利夫兰、圣路易斯、匹兹堡、密尔沃基、底特律和哈特福德(图4中用灰圆圈标示)这样的城市既没有扩张,房价也没有强劲上涨,(除了哈特福德之外)也未能吸引移民。它们的经济表现(匹兹堡除外)也低于标准水平。
图5显示了房价上涨与人口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尽管在各个大城市地区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可以通过利用新的“可开发”土地或增加现有土地上的住房存量(例如,通过填充或更高的密度)调整住房供给。在图6中,可观察到人口增长与已开发地区的扩张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这与许多快速增长的美国大都市向其周边地区扩张的方式一致。
但是,一旦我们考虑了“可开发地区”与房价之间的联系,如图7所示,就没有了相关性。快速发展的城市地区在城市边缘向外扩展,可能会受益于可开发边缘的低土地价格,从而降低其平均住房价格。但是,我们无法在衰落的城市地区(例如锈带城市)中发现这种影响,因为那里有大量的闲置土地。无论如何,在成熟的大城市地区,大都市边缘已经远离核心地带且被长期占用(有时遇到自然地理障碍),从而增加了通勤时间。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宣布发展公共交通的政策目标,还要在城市核心地段地价坚挺的已开发土地上增加住房供给。为什么这类大都市核心区的住房总供给变化不太可能通过社会和空间的涓滴效应降低总体住房成本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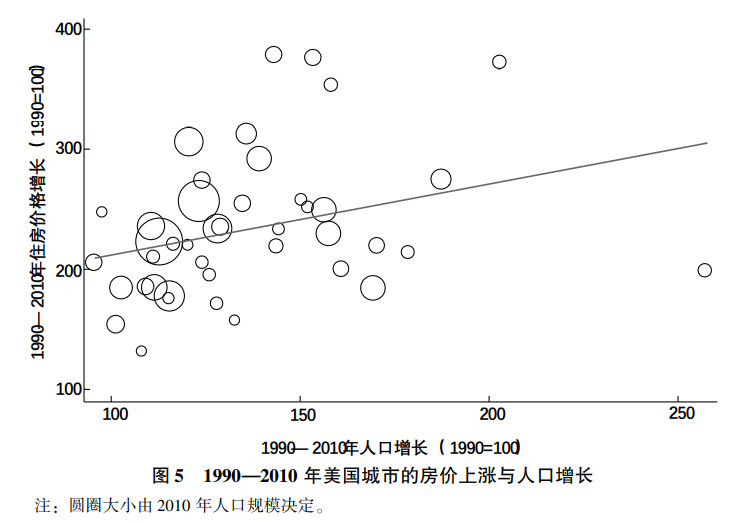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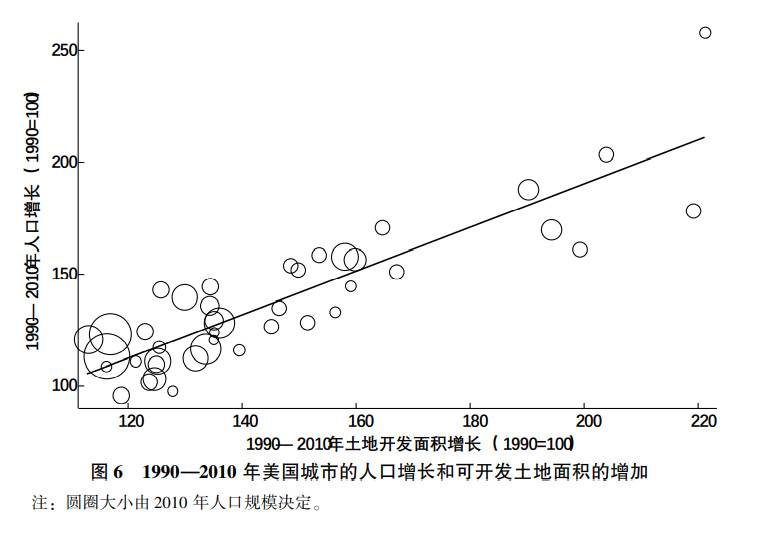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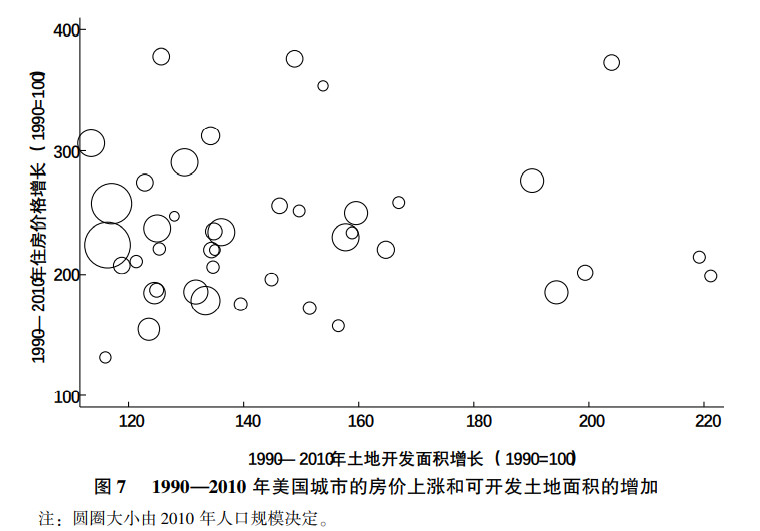 |
在下文中,我们认为决定这些城市房价和可负担性的要素是被忽视的工作和收入结构,而非住房总供给政策。
收入和城市规模驱动房价
昂贵的城市地区和广阔的城市地区之间的差异在于住房需求结构背后的收入和财富。2001年至2013年,旧金山湾区超高收入家庭的比例从17%增加到27%(Bronstein,2017)。这是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集聚了高技能、高薪工作。(①从长期视角看,旧金山的工资变化可以解释住房成本的大部分变化(Fischer,2016)。)在高薪和高便利度的大都市区,扣除住房成本后的实际收入平均比低薪城市地区高出15%(Kemeny and Storper,2012)。这些繁荣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通常很高,这是由于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越来越大造成的(BaumSnow et al.,2017)。低技能的工作岗位大部分由国际移民填补,因为低技能的国内工人已基本上停止向这些地区移民。外国移民有各种各样的住房策略,从高密度、人满为患、不合标准的住房到长途通勤。尽管存在这些假定的障碍,但非技能工人和技能工人仍继续向高收入城市迁移(Lindley and Machin,2004)。大型城市群人口增长的另一个要素是年轻人。年轻人尚未处于技能等级的最高层,但愿意在短期内忍受困难条件,以积累他们在(机会)阶梯上的经历(De la Roca and Puga,2017; Galeser and Maré,2001;Jayet,1983)。
让我们回到技能水平较低的国内劳动人口上来,主流住房观点认为劳动力在区域间流动受到住房成本的阻碍。奥托(2019)指出,美国技能水平较低的成年人的小时工资不再像以前那样随人口密度上升而急剧上升,而技能工人的小时工资与人口密度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技能鸿沟:城市地区具有大学学历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例比农村地区高20个百分点。1970年,这一差距仅为5个百分点。几十年前,中等技能的工作聚集在大城市,而低技能的工作在农村最为普遍。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农村地区比城市地区更容易找到中等技能的工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同类型工作岗位(创新型/集聚型/非常规型相对于常规型)的区域间差异已经影响了房价的地理格局。新经济地理学将这一差异正式建模为繁荣的大都市地区之间的空间分割(spatial split),这些大都市地区聚集了几乎不受空间竞争影响的创新型高薪产业,而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以可贸易性强的常规活动为主,并受到全球竞争的影响(Venables,2018)。
繁华都市区(如波士顿、旧金山、纽约或大多数欧洲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也出现在大城市内部:住房偏好越来越倾向于获取位于市中心的城市便利设施、交通和就业机会。这种现象推高了繁华大都市区中心地段的房价,导致与市中心越近就越需承受不利的房价(Partridge et al.,2009)。这是从20世纪中叶到20世纪后期的模式转变,彼时技能工人的就业集聚力量较弱。相比之下,在成功的阳光地带大都市地区,如亚特兰大或休斯敦,城市核心居住区较弱,因此对更中心地段的需求也较弱。此外,如今的技能工人不再像前几代人一样,在生命周期的同一时间点移居郊区。根据奥托(2019)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壮年的外出移民人数下降了50%—75%。这可能是由于当今城市的机会阶梯越来越长、越来越陡峭(De la Roca and Puga,2017),以及主要大都市地区通勤的时间成本较高。与以前相比,内城区的竞争更加激烈,这强化了如下观念,即放宽限制性分区可能会使内城区“贵族化”,但对于提升技能水平较低人群的住房负担能力收效甚微。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评论区 0
本篇文章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