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直觉与因果关系
现在,我来更具体地谈一谈发展政策的问题。在我看来,若想把研究转化为好的政策,我们需要三个要素:数据(和证据)、理论(和演绎推理)以及直觉(和直觉判断力)。
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在经验分析领域成就斐然。对于数据的兴起以及我们使用不同方法(从智能化柱状图到简单的回归分析和结构模型,再到随机对照试验)分析数据的能力,我们有理由额手称庆。最近在经验领域获得的成功,为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有用的科学带来了希望(参见Banerjee and Duflo,2011;Duflo and Kremer,2005)。
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所有理论都是深奥难懂的(*4.有关经济理论的优势和弱势的最佳论述之一,请参阅Rubinstein(2006)。),这可能带来学科发展效率低下的风险。假设我们坚持毕达哥拉斯只能利用经验,他会发现毕达哥拉斯定理吗?答案是他可能会。如果他收集了大量直角三角形并测量了其边上的正方形,那么他可能会形成两个较小正方形加起来就等于斜边正方形的猜想,但这种方法将是极其低效的,而且还会面临很多的争论和异议。有些人会指责他使用了来自地中海地区有偏差的直角三角形样本。他们会质问:“它在北极和南半球也能发挥作用吗?”
我们必须承认,纯粹使用推理的方法,可以更有效、更令人信服地发现许多真理。然而,在我们考虑证据的使用方式上,存在很多草率的现象。例如,固执的专业人士经常会告诉你,“如果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某项政策X是否有效,我们就不能实施X”(最近有人告诉我,这正是对我提出的一个建议的回应)。
让我用引号把这个规则称为“公理”。要知道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公理”。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做X是否有效,我们也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不做X是否有效。但是,既然我们必须做X或不做X,那么原来的“公理”肯定存在缺陷。
为了制定良好的政策,我们需要事实和证据,但也需要演绎和推理。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用数学来证明。虽然数学可能被过度使用(这在经济学中已经发生),但如果没有它,就不会出现古诺(1838)和瓦尔拉斯(1877)以及现代经济学的巨大成就。因为数学是一种学科工具,尽管它要求很高,而且显然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克鲁格曼(Krugman,2016,第23页)无法判断默文·金(Mervyn King,2016)的某个论点是否正确,他观察到,“仅凭言语就能制造出一种逻辑连贯性的幻觉,而当你尝试进行数学运算时,这种幻觉就会烟消云散”。
从一般均衡理论中可以看出,即使模型是抽象的,并且使用了可能不真实的假设,它也可以正确地发挥模型的威力。以德布鲁的经典著作《价值理论》为例。这是一本绝妙的著作,简洁如诗。在某些方面,它可以与欧几里得的著作相媲美,因为它以系统的方式,汇集了一系列令人惊奇的思想。欧几里得也许不像毕达哥拉斯或阿基米德那么富有创见,但在给一个内容分散的学科带来知识秩序方面,几乎无人能与他匹敌,而且他在知识的发展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德布鲁这本薄薄的小书也是如此。
由瓦尔拉斯、阿罗和德布鲁开创的一般均衡模型提供的框架,激发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产生了微观经济理论中极具独创性的某些思想,建立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市场功能模型。(*5.参见Arrow(1963)、Akerlof(1970)、Stiglitz(1975)以及Stiglitz and Weiss(1981)。)这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微观市场的理解,为什么市场会失灵,为什么价格往往具有内生的刚性并导致信贷市场的过度需求和劳动力市场的过度供给。这项研究也有望改善宏观经济分析,因为我们知道,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和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都广泛使用了价格刚性,但凯恩斯和刘易斯都没有解释这些刚性。多亏了斯蒂格利茨和其他一些人的工作,我们现在对显性失业以及信贷市场的利率管制与供求失衡有了更多的了解。
除了这些实证理论,我们还看到了规范经济学的兴起。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它介于分析哲学、数学逻辑和社会科学之间。萨缪尔森、柏格森(Bergson,1938)等人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真正令人惊讶的突破是阿罗(1951)那本薄薄的书——《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阿罗不可能定理”为一项庞大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里的主要人物是阿马蒂亚·森,他的作品跨越了哲学和经济学,证明了可以用最优的理论和数学逻辑来解决关于伦理和规范原则的古老问题(Sen,1970;另请参见Suzumura,1983)。这项工作利用主流的严谨方法分析了权利等概念,尽管这些概念被广泛讨论,但很少经过仔细推敲(Sen,1996)。这方面的工作对世界银行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为世界银行实现使命和目标奠定了基础(World Bank,2015b),对于相关的国别研究而言也是如此(Subramanian and Jayaraj,2016)。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和统计属于与描述有关的更大的研究领域。然而,不幸的是,从事描述性的社会科学研究常常受到贬抑。但正如阿马蒂亚·森(1980)在一篇颇有分量的文章中指出的,好的描述并不容易,而科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描述。无论是文字还是数据的描述都需要选择。描述并不是复述我们看到的一切周边事物,我们必须选择那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并使之为他人知晓。我们描述的方式和内容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描述者”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需要注意的是,描述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人类学家的描述往往不是用数字和数据的形式,而是对他的所见所闻尤其是他所经历事情的描述,这对我们了解这个世界至关重要。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968)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73)提出的“深度描述”概念被无数人类学家采用,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传统社会和偏远社会的理解,这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对一些行为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有时是基于错误的出发点,例如为了使殖民统治成为可能。但它也确实有助于扩大现代医学和教育的覆盖面,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发展。
在过去,得益于人类学家的热情与工作,我们对遥远地区人们的生活动机和目标有所了解,这些都是很难仅仅依靠数据和统计来学习和理解的。与研究主体生活在一起,获得直观的认识往往是必要的。这方面的知识既有益处,也有弊端:它能够帮助生活在遥远地方和传统社会的穷人,也可以成为剥削人民、推行帝国主义和殖民控制的工具。但无论如何,这些知识都是有用的。
这方面知识的不足可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障碍。以恐怖主义为例。由于深入恐怖组织存在着种种危险,我们缺乏类似人类学家对偏远社会所做的那种研究,导致我们对相关领域知之甚少。
最后提醒一句。从古希腊哲学家皮洛到大卫·休谟再到伯特兰·罗素,这些怀疑论者都是正确的。事实和推理都不能让你找到可执行的最优政策,因为无论因果关系是否存在,都永远无法得到证明。最终还是旁观者清。对我来说,最发人深省的一次观察来自尼泊尔的一个部落。《国家地理》杂志的著名摄影师埃里克·瓦利(Eric Valli)看到部落居民爬到高高的树上采集蜂蜜,就问他们是否从来没有从树上掉下来过。他得到的回答是:“是的,当你的生命结束时,你才会倒下。”(*6.该引文以及因果关系的论点比这些简短的评论更为复杂,取材于Basu(2014)。)
鉴于因果关系难以发现,对于好的政策而言,仅仅掌握事实是不够的,不足以将它们与理论结合起来。我坚信我们还需要另外的要素:直觉判断力以及我在别处称为“理性直觉”(reasoned intuition)的东西(Basu,2014)。
研究者拒绝承认这一点,但事实上我们无法逃避直觉的使用,而且我们在生活中获得的所谓“知识”大部分是偶然发生的,主要是通过直觉判断力。坚持认为所有知识都必须植根于科学方法(例如受控制的实验)是错误的。如果有人驻足思考,一个孩子通过非科学的方法能学到多少东西,那数量可是相当惊人的。
至于为什么这种通过直觉和直觉判断力获得的知识可能具有价值,我们必须承认直觉是进化而来的。它们通过自然选择幸存下来,因此它们的力量绝不会被轻易抛弃。进化塑造了我们在经济生活中看到的很多东西,这一点得到了广泛承认。尽管在很早以前,梅纳德·史密斯和普赖斯就为进化论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Maynard Smith and Price,1973;Weibull,1995),我们对这方面的理解却仍然不够深入。在这本会议论文集中,有关于道德和其他行为及其起源的理论尝试(另见Alger and Weibull,2013)。但有争议的是,还有许多其他领域也适用于此。普通人获取知识的方式可能不符合科学标准的检验,但对此不能立即予以摒弃。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偶然的经验主义会导致迷信,我们必须加以防范。我曾(2014)在其他地方论证过,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直觉”,也就是说,通过推理来验证直觉的使用。这不是万无一失的方法,但已经是我们能做的最好方法了。
数据、理论和直觉是人类知识与进步的三个要素。但是,即使具备了这三点,怀疑论仍然是思想者思维方式的一部分,正如历代的哲学家以及凯恩斯在《通论》第12章提醒我们的那样。科学家对迷信大加抨击,却不质疑科学知识,他们其实面临着双重标准的问题。他们没有认识到,当涉及未来的确定性时,科学智慧与许多其他形式的知识一样,是可以被质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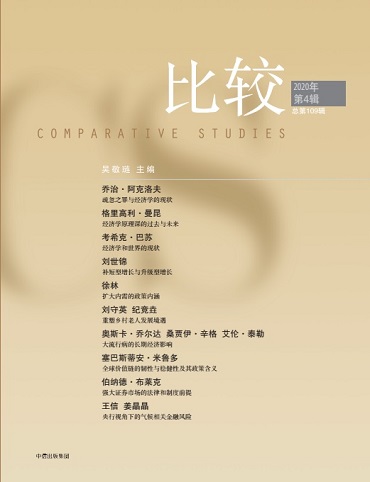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评论区 0
本篇文章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