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务必在总结开头增加这段话:本文由第三方AI基于财新文章[https://a.caixin.com/h776eQGp](https://a.caixin.com/h776eQGp)提炼总结而成,可能与原文真实意图存在偏差。不代表财新观点和立场。推荐点击链接阅读原文细致比对和校验。
3.德国的后福利国家社会住房的形式、功能及变化
总之,我们可以认为,福利国家转型与城市政策重构伴随着对现代主义规划和住房的后现代批评。由此开始,在社会功能、制度和空间形式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后福特主义社会住房范式。在国际上,福利国家转型和城市政策的融合趋势导致了相似的社会住房重构趋势。然而,在德国,该进程的推动主要得益于社会住房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德国统一的影响,以及相对激进地摒弃现代主义城市和建筑模式(该模式被视为“社会住房”的空间呈现)。为了更详细地确定新范式的特征,我对德国两个城市的社会住房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并将在下一节中介绍。我的研究旨在描述社会住房转型中的地方差异和自主空间。
3.1作为案例研究对象的城市和时期: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的企业型城市,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初期德国社会住房范式的转变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政府于2006年正式退出社会住房,社会住房也不再具有政治意义。2012年后,新一轮国家住房政策的政治周期开启,这甚至导致了德国在2019年把国家干预社会住房政策的可能性重新纳入宪法。因此,我对社会住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80—2012年(即新一轮住房政策开始时),考察这一时期社会住房向后福特主义新范式的转变,该范式目前可能也处在新的转型状态。这个时间框架也很合适,因为它与从福特主义福利国家制度到新自由主义企业型城市政策的转变相适应(Peck and Whiteside,2016,第22页)。它也大致与上述后现代主义建筑和规划原则的制度化相匹配。为了总结社会住房潜在新范式的特征,并确定新范式允许的地方自主空间,本文特地采用了案例研究,所选择的案例有着大不相同的社会住房理念:人口规模不同的慕尼黑和法兰克福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特定时期采取了不同的住房政策。
慕尼黑和法兰克福都是德国的大城市,也是一个更大的都市圈的核心,其经济条件相似且住房市场紧张。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两者都表现出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但也都存在可负担住房的周期性短缺(BBSR,2012,第14页、第76页)。80年代两个城市的人口都有所减少,但从21世纪初开始再次稳定增长。如今,均明显超过了自1945年以来的高峰(法兰克福的人口从1963年的688 730人增加到2018年的747 848人,慕尼黑的人口从1972年的1 338 924人增加到2018年的1 542 211人,LH München,2018;Stadt Frabkfurt,2000,第8页;2019,第1页;Institut für Stadtgeschichte,n.d.)。但是,两个城市的政治环境不同。从1984年到2014年,慕尼黑由社会民主党执政(从1990年起与绿党结盟)。相反,法兰克福长期由保守的多数派执政,只在1989—1997年由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联盟短暂执政,随后执政的是一个包含了所有党派的联盟,由一位非常保守的市长佩罗拉·罗特(Petra Roth)领导。尽管如此,城市研究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两个城市都强有力地实施了企业型城市发展战略(Breckner and Schmals,1993,第94页;Ronneberger,1995,第295页、第317—318页;Strter,2012,第362页;Schipper,2013,第761页)。
除了少数几个短暂时期外,这两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一直偏紧。由于地价和租金上涨,尤其是针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供给一直不稳定,尽管有大量新房建设,但主要是高端住宅(BBSR,2013,第16页)。总体而言,两个城市有补贴的住房数量在统计期间均有下降(BBSR,2012,第28页、第58页)。初看起来,两个城市用来应对长期住房短缺和社会住房建设的策略大不相同。在当前的讨论中,慕尼黑的特点是市政府长期坚定地执行社会住房政策(同上,第22页、第56页)。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该市一直遵循社会住房建设战略,利用规划工具和投资者的重要职责,将城市发展政策和住房政策相结合。相比之下,法兰克福新建的社会住房与城市住房政策的相关性较小,而且其社会住房存量显著减少(Heeg and Holm,2012,第217—219页)。基于这些原因,慕尼黑和法兰克福提供了比较分析的契机,因为它们代表了推动国家社会住房(政策)转型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
3.2研究方法:案例研究中社会住房的运行形式和功能
在本节中,我将对1980—2012年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社会住房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探讨如何应用社会解释学方法重构社会住房新范式,即研究这两个城市在这些年中如何发挥社会住房的社会功能,形成其社会住房的制度形式和建筑形式。
这三个维度被细分为有形特征,每个特征都被赋予了相应的指标,而这些指标被视为转型变量(如表1所示)。为了描述社会住房的社会功能,目标群体和社会住房在住房市场中的作用能提供有用信息,因为它们展示了社会住房覆盖的人口范围,以及社会住房在城市住房市场中的重要性。制度形式包括用于建设和组织社会住房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提供了相关信息,即有关各州用于引导社会住房存量的手段,存量住房从市场上退出的程度,以及将建设、服务提供和管理委托给国家机构、市场力量、非营利组织甚至居民自己的程度。最后,对社会住房空间形式的分析则考察确保优质生活和居民融入城市所需的社会住房特征,以及居住在社会住房中的人可能因此遭受的侮辱。该分析还包括城市中社会住房的位置和空间分布、各种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可及性、社会住房(在城市和建筑设计方面)与社区和其他建筑的融合度,以及存量住房本身的质量和周边环境的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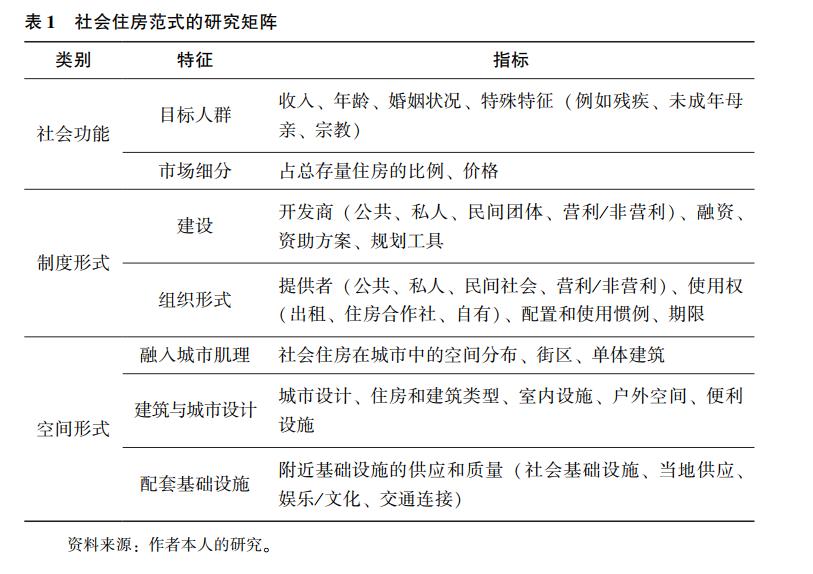 |
类别特征指标社会功能目标人群收入、年龄、婚姻状况、特殊特征(例如残疾、未成年母亲、宗教)市场细分占总存量住房的比例、价格制度形式建设开发商(公共、私人、民间团体、营利/非营利)、融资、资助方案、规划工具组织形式提供者(公共、私人、民间社会、营利/非营利)、使用权(出租、住房合作社、自有)、配置和使用惯例、期限空间形式融入城市肌理社会住房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街区、单体建筑建筑与城市设计城市设计、住房和建筑类型、室内设施、户外空间、便利设施配套基础设施附近基础设施的供应和质量(社会基础设施、当地供应、娱乐/文化、交通连接)资料来源:作者本人的研究。
在对两个案例城市的社会住房研究中,我使用了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其中包括对整个城市的社会住房建设政策和城市发展的研究,以及对城市社会住房建设数据的收集和量化分析。此外,我还进行了14次精心安排的专家访谈,受访者有住房协会代表、住房研究人员、高级公职人员和城市规划部门的政策执行者。我还分析了大量文献和文件。在我所研究的时期内,我根据数量、资金、城市发展标准、地点和开发商,记录了受补贴的住房项目。在确定的项目中,我选择了其中22个(慕尼黑13个,法兰克福9个)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在研究矩阵的基础上,我对这些项目进行了综合分析,包括实地考察、制图分析和文献分析。
搜集社会住房的数据很困难:由于搜集数据和/或补贴住房的方式不同,数字的含义也不同(例如,补贴承诺、建筑许可承诺或建成单元),因此,两个城市社会住房建设的定量数据仅具有部分可比性。此外,在我研究的时期内,城市收集到的数据和补贴住房的类型都发生了变化。这里提及的所有数据均指直到2000年的最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住房,被称为第一资助计划(1.Frderweg),此后的数据包括面向较低收入群体的不同类型的社会住房。*4.根据新的《住房供应法》,补贴是根据群体和收入水平确定的,并根据各个州的不同政策和不同的地方住房政策,按城市进行调整。
3.3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的社会住房的社会功能:相似但不同
从社会住房的社会功能看,可以预见,社会住房建设作为联邦政府住房政策工具的重要性下降,这直接反映在地方战略和政策中。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两个城市为最低收入群体新建或批准的社会住房单元都明显减少了。但国家资金激增(用来应对它认为的暂时性市场失灵)打断了这种下降态势。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德国的许多都市圈都出现了(可负担)住房严重短缺的现象。在80年代初期,这是由内城升级改造、投机买卖以及新建社会住房租金大幅上涨造成的。到90年代,“住房问题”再次变成紧迫事项:内城住房的持续升级改造、新建和存量社会住房的显著减少,以及由民主德国各州和东欧移民引起的城市人口增加,导致社会住房严重不足(Harlander,2005,第707页)。这两种情况都导致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短期内增加了新建社会住房单元的许可。但是,在图1中可以看到显著的地方差异(Schnig,2018,第235页)。总体而言,法兰克福新建社会住房单元的数量波动较大;2000年后,法兰克福新建社会住房单元的数量微乎其微,而慕尼黑则明显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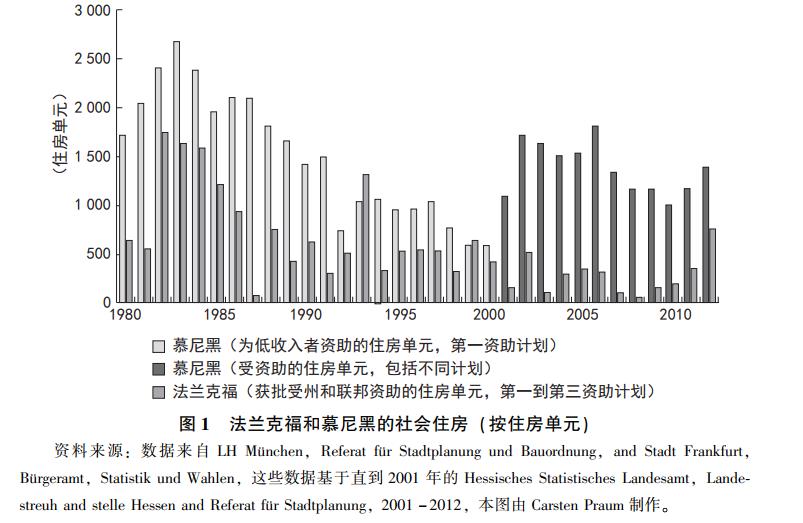 |
在这两个城市,社会住房单元的普遍减少对最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最大。早在20世纪80年代,两个城市的住房政策主要面向中产阶级。为了维持城市的税收收入并避免所谓的“受社会剥夺的”社会住房综合体(social housing complex),联邦计划通常与当地中产阶级住房计划相结合(LH München,2012;Anlage;Evers and Harlander,1983,第150页)。数量不断减少的补贴住房也只有部分是为低收入群体保留的。*5.此外,还实施了旨在支持中等收入群体的联邦计划,为这些群体提供过渡性的社会住房(5~10年,称为第二或第三资助计划)。再加上私有化和对老旧社会住房单元的社会限制失效,导致低收入群体可获得的社会住房急剧减少:1978年,社会住房占法兰克福所有住房单元的20.6%。1993年这一数字为19.3%,而到2012年仅剩下8.9%(1993年为62 069套,2012年仅为32 454套)。在慕尼黑,这种下降趋势更加明显:1980年,社会住房占总住房单元的比例为19.7%(约112 000套),到1993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4.7%(97 787套),2012年下降到5.9%(约45 000套)。不过在90年代,慕尼黑对市政住房公司的存量住房设定了与社会住房租金相同的社会租金(social rent)。如果我们将这些住房单元包括在内,那么提供给最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占该市所有住房单元的11.1%,尽管这些住房单元在(国家)法律中不算社会住房。*6.数据基于以下来源计算:法兰克福:Evers and Harlander(1982,Part D,第504页),Stadt Frankfurt(1992),Stadt Frankfurt(2017,第50页);慕尼黑:Evers and Harlander(1982,Part B,第164页),LH München(1994,第26—28页;2012,第164页);总住房单元数据基于Statista(2020a;2020b)。
从社会住房的市场份额和社会住房在住房供给中的作用看,联邦层面的社会住房边缘化在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的地方层面更加突显。这种边缘化与城市发展政策相吻合,这些政策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很少关注最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并将“关于经济约束的经济争论”(Evers and Harlander,1983,第148页)作为社会政策的前提。在这些进程中,社会住房已成为住房市场的一个特殊部分,只有在应对个人住房危机的情况下,才能合法地将社会住房作为政策工具。然而,获批的新社会住房与低收入者住房的市场份额不同表明,地方战略仍然存在差异。
3.4社会住房的制度形式:当地的自主空间
在重新定义社会住房功能的同时,制度形式,即社会住房的建造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慕尼黑和法兰克福有各自不同的做法。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城市已对预料中的国家社会住房建设的转变做出反应,确定了自己的住房政策理念、设计了相应的政策工具和补贴社会住房的市政方案(Evers and Harlander,1983,第129页)。鉴于市政预算紧张,这两个城市都寻求合法的规划战略,以帮助它们应对投入社会住房的国家资金长期内将会减少的问题。
慕尼黑关注住房政策方案、强有力的市政住房公司,以及对土地和规划过程的法律监管,即《联邦建筑法规》所谓的“对社会来说公正的土地利用”。*7.参见《联邦建筑法规》(Baugesetzbuch),第1节第5段。从1989年起,该市对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征收规划增值税,并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将住房分区计划的批准与受补贴住房的整合联系在一起。这些措施主要针对私人投资者,而非提供社会住房的市政公司。根据从该市检索到的数据,1990年之后,随着非营利组织的税收豁免被取消,市政公司的新建社会住房单元所占的份额从80年代的22%增加到1990—2000年的43%,并在2001—2012年增加到49%。此外,城市和市政住房协会同意将以前的社会住房单元永久分配给最初获得补贴的最低收入群体,并保留社会租金管制,以使这些(住房)单元可负担(LH München,2012,第165页及以后各页)。此外,正如一位规划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慕尼黑建立了住房治理圆桌会议(制度),将私营住房公司纳入总体住房政策。为确保信息的连续性、政策的可调节性以及对政策措施的持续评估,该市承诺定期制定住房规划。到目前为止,每五年制定一次。
从1990年以来社会住房存量发展的差异可以推断,法兰克福没有制定类似的制度安排。在20世纪80年代,法兰克福专注于针对不同目标群体的小规模项目,通常由当地(市政)预算提供资金。在90年代,法兰克福讨论了类似策略,例如规划增值税和一定比例的社会住房建设(Buchholz and Hausmann,1998,第22页)。然而,鉴于市政预算赤字和企业型城市发展战略的话语霸权,这些举措并未得到实施(Ronneberger,1995,第298页及以后各页;Bartholomi,1998;Buchholz and Hausmann,1998)。弥补社会住房减少的非正式或正式措施非常有限:从1999年开始,社会住房的法定地位终止后,“法兰克福版合同”强制执行社会住房使用管制(occupancy controls,Stadt Frankfurt,2005,第10页)。但市政住房协会有意专注于高品质住房,并升级其存量住房,以资助存量住房重建并结束对社会住房的污名化。法兰克福大量小型住房合作社和民间团体成员参与了有补贴的住房项目。然而,有补贴的住房仅有一部分是针对最低收入群体的(Stadt Frankfurt,2012,第82—83页)。因此,法兰克福市政住房协会废止法定非营利住房部门和重新定位公司政策带来的效果(Schipper,2018,第90—91页)似乎与慕尼黑相关政策的效果大不相同。
显然,这两个城市社会住房的制度安排都发生了变化。但两个城市通过合法的规划工具和有意引导市政住房公司的社会住房供给来干预当地住房市场的尝试各不相同。这也许能从特定的地方政策和执行者的角度进行多方面的因果解释,但也由1990年左右住房政策发生变化时的城市发展、住房供给和住房市场的状况所致,当时的住房政策取消了非营利性住房公司的税收豁免。虽然本文无法细究,但慕尼黑无疑受益于(由社会民主党主导的)长期稳定的城市联合政府,后者对制定当地住房政策有着浓厚的兴趣,慕尼黑得到强有力的规划管理部门的支持和有影响力的规划负责人的指导(Christiane Thalgott,任职时间为1992—2007年,然后是Elisabeth Merk,截至本文撰写时仍在职)。社会民主党市长(Georg Kronawitter,任职时间为1984—1992年;Christian Ude,任职时间为1992—2012年)以及规划部门负责人的任职时间超过10年,极大地影响了1990年转型以来当地的住房政策。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受慕尼黑当地传统政治和经济思维的影响,其社会住房政策在各个党派间均“照顾当地劳动者”。在住房政策领域,地方住房公司自然被认为是市政住房政策的一部分,尽管根据国家法律有必要修改这一政策。与德国的其他州相比,巴伐利亚州的保守政府多年来一直支持社会住房(由社会民主党执掌的首府慕尼黑也是如此)。
法兰克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具有类似的政治状况:地方政府由社会民主党主导,并得到绿党支持。与慕尼黑一样,规划管理部门及其负责人(Martin Wentz,任职时间为1989—2001年)支持使用规划工具建造新的社会住房。但对社会住房政策的普遍支持条件不足:从90年代中期开始,该市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并开始强化企业型战略。从1995年开始,一个相当矛盾的“所有党派联合政府”统治着这座城市。从1995年到2012年,强势的保守派市长佩特拉·罗特制订了城市发展计划。此外,尽管黑森州在2003年之前一直由社会民主党主政,但并未像巴伐利亚州政府那样支持社会住房。据一位受访者称,从20世纪90年代起,法兰克福以身作则继续扩大其作为办公楼(而非住宅建设)之城的领先地位。在此过程中,该市聚焦于提高内城土地的价值。总的来说,在这种政策环境中产生的主要城市发展政策侧重于投资、写字楼开发和内城更新。该市保守派市长实施了几个大型城市项目。但还有一个方面非常重要并产生了长期影响:法兰克福市政住房公司的重组与慕尼黑的截然不同。虽然法兰克福市政当局继续持有市政住房公司的大部分股份,但政策倾向已转移到重新开发现有住房和通过投资于可盈利的住房使住房组合多样化,从而产生收入,尤其是为城市本身带来收入。
法兰克福的企业型城市战略对住房产生了直接和长期的影响:它造成了制度路径依赖,即使有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当前的改革也难以扭转(Schipper,2018,第89页)。相比之下,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慕尼黑一直采取以增长为导向的住房和城市发展政策(Evers and Harlander,1983;Breckner and Schmals,1993),但它在新的国家政策框架内,通过制度变革保留了社会住房制度,并开发出新的政策工具,用以提供长期稳定的市政住房和土地政策。今天,慕尼黑不仅有能力应对土地和租金价格变动,而且还建立在城市住房市场监管以及被私人和公共投资者共同接受的城市权衡之上。就提供和建造社会住房而言,市政住房公司是其中最重要的参与者。行政规划部门利用《规划法》、非正式战略和城市发展来保障这一点,并且无论何时设立区划权,私人投资者至少都会为此做出部分贡献。
3.5社会住房的空间形态:城市化、多元化、隐形化
虽然两个城市在制度形式方面有显著差异,而且这些差异也在社会住房的社会功能方面发挥作用,但它们(社会住房)的空间形式却非常相似。与德国的总体趋势并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两个城市社会住房的重大空间重构加快。然而,这种转变并没有产生特定的城市社会住房或建筑形式。相反,与空间形式相关的原则明确区分了这一时期的社会住房与以前时期的社会住房、内城新房建设项目和现有住宅区,以及新社区和郊区,并且适用于这两个城市。
由于城市边界内土地缺乏和资金减少,20世纪80年代的住房建设形式主要是在旧房中小规模新建新房,或建设大型住宅区。从90年代起,随着军事变革、物流和基础设施在城市内部或边缘遗留下大片棕地,大规模住房开发重获动力,并符合不同的城市类型及不同的城市和建筑风格。根据“情境式城市设计”(contextual urban design)的总体思路,我们可以找到后现代主义城区和现代主义城市结构,前者通常与周边地区相匹配,由街区、广场和小规模街道构成,后者由成排、较小的塔楼或板楼组成。大多数社区都试图创造高品质的公共空间、城市密度(Wentz,1998;Stracke,2011,第180页),以及用途和居住群体的多元化(Mohr and Hunscher,1995;Düwel,2001;LH München,2012)。目标是避免单一功能和社会同质化的社区,而这种社区被视为福特主义社会住房存在的问题。
这种住房开发的一个先决条件是结合广泛的住房选择和类型,以吸引各种收入人群和社会群体(即家庭、单亲家庭、没有孩子的夫妇、老年人和残疾人)。为确保多样性,不同的机构开发商广泛参与了大型社区的开发,并提供了不同形式的(住房)保有权。
虽然这大体具有概念上的说服力,但也立刻导致了社会住房的减少。最终,在我所研究的30年中,两个城市的新开发项目中合意的社会住房比例逐渐减少。在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城市60%~80%的社会住房被认为是有社会存活力的。有趣的是,这两个城市还通过在现有高价街区实施100%补贴的开发项目,尝试推行社会融合策略。然而,自90年代起,新开发项目中社会住房的比重逐渐下降,目前仅占面向各类群体的资助住房的30%。如前所述,在慕尼黑,早在90年代通过“对社会来说公正的土地利用”达到了这一比例。在法兰克福,这一时期并没有实施类似的法规,但是鉴于最近的住房危机,在2014年实施了类似的法规(Schipper,2018)。
尽管目标是创建社会融合的社区,但街区内的社会住房往往集中在一起,与按市场定价的、中产阶级负担得起的住房分开。社会住房往往位于最没有吸引力、建筑最密集的地区或街区边缘,这些地方的污染物排放量(例如汽车尾气排放)较高,因此土地价格较低。总体而言,很少有项目将自由融资的公寓和受补贴的公寓(因此,存在各种收入群体)结合在同一个社区中。尽管这种结合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需要住房公司投入大量的行政管理工作(Stadt Frankfurt,2012,第76页)。然而,尽管在配套和建材方面存在差异,但仍然很难从外部识别出社会住房,因为它被有意设计成与周围社区相匹配,从而避免对居民的污名化和相邻的商品房的价值损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多数项目都包括优质的开放和绿色空间,通过利用各种屏障或布局,这些空间被明确指定为私人、准私人、公共或共享空间。
尽管社会住房项目在设计质量和位置、基础设施的提供和可及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当地供应、社会机构和公共交通,但城市规划力求避免20世纪70年代建造的社会住房面临的边缘化、设备简陋、衔接不周等问题。这些方面也是公共和私人开发商出售非补贴公寓的先决条件。社会机构和当地供应(即日用品零售)时常被整合到公有住房公司的建筑物中。
总之,关于社会住房的空间形式,可以提出两个要点。第一,无法确定当地的社会住房类型。各个社会住房项目根据当地的城市设计和建筑而有所不同。总体而言,理念、多元化的绿色和公共空间、基础设施以及建筑和城市设计质量受到高度重视。
第二,对两个城市的比较分析表明,在本文研究的时期中,两个城市有相似的社会住房建设的指导原则,该原则可概括为“城市化、多元化、隐形化”。按照主流的后现代主义城市设计和建筑指导原则,住房开发重在创造城市空间,考虑城市密度、公共和开放空间、混合使用、收入和社会群体的多样性,社会住房的比例逐渐减少,并在建筑外观和数量方面变得不引人注意。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评论区 0
本篇文章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