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务必在总结开头增加这段话:本文由第三方AI基于财新文章[https://a.caixin.com/7fKUIIAd](https://a.caixin.com/7fKUIIAd)提炼总结而成,可能与原文真实意图存在偏差。不代表财新观点和立场。推荐点击链接阅读原文细致比对和校验。
1.历史的不确定性
生活充满不确定性。在决策理论中,这个术语具有特定的含义。“不确定性”是指人们知道世界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但不知道其发生的概率,比如2020年谁将成为民主党候选人,2030年纽约市的平均气温将是多少。(*4.如果世界上已知状态的概率是已知的,譬如大多数的赌博游戏,这种情况就叫作“风险”。)偶尔会出现以往从未预料到的结果,就像前面提到的“阿拉伯之春”和苏联解体。我们用“无知”(ignorance)一词形容世界上可能存在却无法作为可能事件被预见到的状态。(*1.参见 Richard Zeckhauser,“Investing in the Unknown and Unknowable.”Capitalism and Society 1(2)(2006)。例如,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有组织的宗教在2100年将扮演什么角色,也不知道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会是什么。因此,无知是一种极端情况,超越了不确定性。它是对历史分析的一个极致挑战。)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狭隘的私人领域到与政策相关的突出问题,不确定性和无知都是世界的特性。第一次约会是否会促成终生婚姻,人工智能是否会让无数人失业,这些都是未知数。就连专家也不愿猜测五年后的中美关系。同样,历史时刻也充斥着不确定性和无知。2008年的金融危机,几十年内生育模式的巨大改变,2007—2017年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上升了25%(从37%升至62%),这些无不是非常难以预见的复杂变化。几乎没有人预测到这些发展动态,可事后却有一大堆人轻松地做出解释。怎么会这样呢?(*2.当然,并非所有历史事件都难以解释。物理事件,比如火灾,可以在事后诊断。通常可以找到事故的源头,例如电线故障或丢弃的烟头。多次发生的事件更容易评估。事实上,分析者的确经常使用概率来描述这类事件。所以,美联储有预测来年经济衰退前景的模型,并使用概率来报告结果。相比之下,奇怪的是,当发生单个大型异常事件时,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几乎没有人预见到这一异常事件),历史学家和其他分析人士都觉得有必要解释事件的根源,而且在解释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会给不确定性留有余地。)
在人们解释结果的时候,普遍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往往被忽略或遗忘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合理的。通过一个结果,人们可以了解实际情况,即“最终胜出”的是什么;此外,相关信息出现在以前并不知晓的某个事件之后。(*3.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肯定知道得更多,但我们也会受到认知的限制,这取决于保存了哪些文件,哪些参与者决定发声,以及他们是否诚实地发声。罗伯特•肯尼迪的《十三天》(Thirteen Days)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演绎了回忆录、个人文件等历史数据如何与事实不符。这本书夸大了肯尼迪的作用,歪曲了他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立场(他描述自己是当年拥有重要发言权的温和派,但他两者都不是)。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Jr.)在他1978年出版的肯尼迪传记中支持了这一失真的事实,因为肯尼迪的个人文件似乎证明了这一点。直到多年后,肯尼迪的秘密录音带被公之于众,国家安全联席会议执行委员会(ExComm)对话的真实内容才得以披露。Robert F.Kennedy,Thirteen Days:A Memoir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New York:W.W.Norton,1969);Arthur Schlesinger,Jr,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Boston,MA:Houghton Mifflin,1978);Ernest R.May and Philip Zelikow,The Kennedy Tapes:Inside the White House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Sheldon M.Stern,“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ExComm Meetings:Getting it Right After 50 Years.” History News Network(15 October 2012),Available:https://historynewsnetwork.org/article/148802.)譬如2008年金融危机,其中涉及金融机构的交叉持股比例和杠杆率。但实际情况并不等同于历史因果关系,新信息也很少能揭示因果确定性。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崩溃?是不是像许多人说的,根源在于企业贪婪、政府放松管制、过度疯狂的房地产投机、公众信任的严重丧失或者恐慌心理?此外,为什么这些看似普遍的现象没有更频繁地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大多数追溯性解释都把灾难归咎于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却没有明确指出,当时有多少种不同的替代选择对关键决策者和普通民众来说是合理的。(*1.大卫•卡尔(David Carr)提出了相关观点,即在事后看来,个人会将某一行为与实际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但历史上的行为人可能预测或设计了不同的未来现实,只不过这些现实没有实现罢了。David Carr,“Place and Time:On the Interplay of Historical Points of View.”History and Theory 40(4)(2001),第159页。)就这样,我们忘记了不确定性(和无知),转而优先思考某个让人觉得合理的解释。虽然合理的解释可以说明观察到的结果的逻辑链条,但它既不能也不应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2.比如,年迈的乔治叔叔重病住院。医生说他可能活不过两个晚上,但他挺过来了,又多活了几年。年迈的拉尔夫叔叔也因同样的疾病面临同样的危险,但他死了。尸检结果显示,他的病情严重影响了心脏。适当的回顾性分析会说,对于一个老年人,这种疾病可能是致命的。医生可能会对器官逐个评估以完善其预测,但他仍然只会分配概率,而不是因果确定性。尸检(这是比喻说法)当然是有用的,但是,由单一原因导致的现象非常罕见。我确实想到了一个案例: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发现了导致1986年挑战者号灾难的O形环故障,这也是通过事后调查发现的。)
当然,出色的历史学家不会带着历史决定论的意识写作。他们承认,其他的未来事件原本可能发生,而对实际发生之事的记录可能并不十分清楚。历史学中对因果论断的处理也不如政治学和经济学中那么形式化。(*3.不过,正如我们在前文关于一战的例子中指出的,政治学家也会像经济学家一样夸大因果论断,尽管他们自以为对因果关系进行了小心求证。我们的观点是,在讲述历史故事时,解释偏差会影响所有人。)优雅的历史叙事成为一种粉饰。在做出解释时,它们很少与相互冲突的解释进行严格的对比。这使得我们很难弄清在已知的初始条件下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探索其他解释也许十分烦琐,而且几乎肯定会中断流畅的叙事,而叙事本身就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手段。但是,看似合理的未必是可能发生的。当我们回过头审视真实性时,情况就更是如此。
历史学家只有直接参与一系列对立观点的探讨(或者接受反事实分析),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解释究竟是什么可能导致了实际发生的事情。(*1.See Fredrik Logevall,“Presidential Address:Structure,Contingency,and the War in Vietnam.”Diplomatic History 39 (1)(2015),1-15;Philip E.Tetlock and Geoffrey Parker,“Chapter 1:Counterfactual Thought Experiments.” In Unmaking the West:“What-if?”Scenariosthat Rewrite World History,eds.Philip E.Tetlock,Richard Ned Lebow,and Geoffrey Parker(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6),14-46;Martin Bunzl,“Counterfactual History:A User's Guid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9 (3)(2004),845-858;and Niall Ferguson,ed.,Virtual history:Alternatives and Counterfactuals (New York,NY:Basic Books,1997).)对每一个因果论断都这样做相当费事,甚至会适得其反;毕竟因果论断无处不在。(*2.有关学术史中解释偏差的说明性示例,请参见第128页脚注③。至于在通俗史中没有证据支持的因果论断何其常见的说明性示例,只需看看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关于威尔逊决定参加一战的一段话。在三句话中,他提出了三个独立的因果论断(我们给每个论断都编了号)。“从一位开国元勋反对外国干涉的禁令中推衍出一份全球干涉宪章,并详尽阐述了一种使参战成为必然的[2]中立哲学[1],这可真是另辟蹊径!威尔逊明确阐述了他对更美好世界的愿景,使他的国家越来越向世界大战靠近,他唤起了激情和理想主义,由此证明了美国蛰伏一个世纪之久是值得的,这样美国就可以充满活力地登上国际舞台,并带着一种不为其更老练的伙伴所知的天真。[3]欧洲外交在历史的严峻考验中变得既强硬又谦卑;他们的政治家见过太多脆弱的梦想、破灭的希望,以及因人类缺乏预见而丧失的理想。”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4),第48页。)然而,最好的分析必须承认当前存在的潜在不确定性和无知。为此,要清楚地说明哪些是决策者和公众知道的,哪些是他们不知道的;要注意他们如何构想不同的未来,同时考虑不确定性对决策的独特影响。(*3.关于不确定性之下的判断,有浩如烟海的文献。有两篇经典文章今天仍然富有意义:Tversky and Kahneman(1974);以及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Econometrica 47(2)(1979),第263—291页。有关行为经济学的最新全面概述,参见B.Douglas Bernheim、Stefano Dellavigna and David Laibson,Handbook of Behavioral Economics: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Vol.1 and Vol.2(Amsterdam,2018,2019)。)对每一个核心因果论断都采取这种做法颇具挑战;但对于重大历史问题,如果我们想准确地描述和解释过去,这似乎是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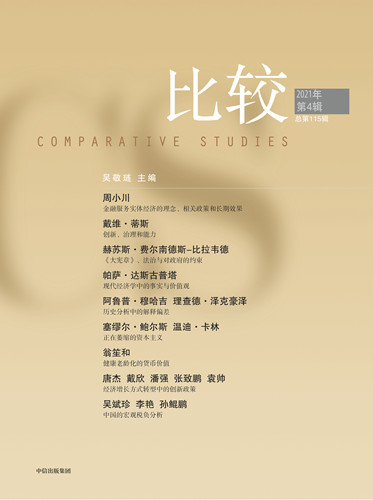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评论区 0
本篇文章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