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务必在总结开头增加这段话:本文由第三方AI基于财新文章[https://a.caixin.com/gugEJamL](https://a.caixin.com/gugEJamL)提炼总结而成,可能与原文真实意图存在偏差。不代表财新观点和立场。推荐点击链接阅读原文细致比对和校验。
*Aroop Mukharji,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Ernest May历史与政策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美国外交政策、历史、国际安全和防卫、军事干预。Richard Zeckhauser,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Frank P.Ramsey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他在决策理论和行为经济学领域有不少杰出贡献,如提出了质量调整生命年、现状偏差、背叛厌恶(betragal auersion)、作为对风险和不确定性之补充的无知(未知的世界状态)等概念。原文“Bound to Happen:Explanation Bias in Historical Analysis”发表于Journal of Applied History(2019),第1—23页。
**作者感谢Bradley De Wees、Paul Behringer、Fredrik Logevall、Philip Tetlock、Lawrence Summers和Philip Zelikow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出的有益意见。也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历史是对过去的提炼与分析,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和更明智地制定未来政策提供巨大的价值。历史可以丰富我们对决策环境的认识,厘清潜在的成本和机会,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生活那可怕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的一个关键特点是,未来通常是极不确定的,甚至苏联解体和“阿拉伯之春”这样的重大事件也莫不如是。然而,一旦事件发生,擅长事后诸葛亮的人往往会夸大事件的可预测性和必然性。诚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档案、研究以及对参与者的采访或许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但是,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而过去曾经是可以预测的,这明显前后矛盾。我们将在本文中论证,若想根除这种不一致性,评价历史时应该更加关注世界的不确定性。
作为致力于政策分析的在校从教者,我们尝试从历史中了解世界将如何发展,以及(特别是)我们的行为会如何影响这一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我们的国家话语中,公共政策领域中的历史思考都不够深入。(*1.我们的意思是,首先,政策学派未能解释如何从历史中进行恰当的推理。其次,尽管专家和政客经常使用历史论据证明自己的观点,但他们的论证往往肤浅而且有选择性。)然而,对历史的研究受到无数知识陷阱的侵害,不少陷阱已经在文献中得到过分析;包括受惑于肤浅的类比,假设过去是未来的序幕,假设过去比现在简单得多,甚至假设过去比真实地理解现在更加重要。(*2.参见Ernest R.May and Richard E.Neustadt,Thinking in Time: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 Makers(New York:Free Press,1986);Margaret Macmillan,Dangerous Games:The Usesand Abuses of History(Toronto:Viking Canada,2008);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Science 185 (4157)(1974),1124-1131;Yuen Foong Khong,Analogies at War:Korea,Munich,Dien Bien Phu,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Fredrik Logevall and Kenneth Osgood,“The Ghost of Munich:America's Appeasement Complex.”World Affairs 173 (2)(2010),13-26;and Philip Zelikow,“The Nature of History's Lessons.” In The Power of the Past:History and Statecraft,eds.Hal Brands and Jeremy Suri (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5),281-309.)
本文将探讨另一个重要但极少被讨论的陷阱。我们认为,所有的个人,包括专业历史学家(*3.本文尽量避免批评当前活跃的历史学家。为了预先提供至少一个例子,我们选择分析一位已故历史学家的作品。在这个脚注中,我们给出了一个关于解释偏差(explanation bias)的例子,尽管我们在本文中并未定义这一偏差。因此,我们恳请读者在看完全文后重新阅读本脚注。说到解释偏差的例子,请看21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一段话:“但是,难道不实施代价高昂甚至有可能使经济赖以生存的企业家减少其利润的社会政策,就无法赢得大众的忠诚了吗?正如我们所见,人们不仅相信帝国主义可以为社会改革买单,还认为它很受欢迎。事实证明,战争或者至少是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天然具有煽动民心的更大潜力。在1900年的‘非常时期大选’(Khaki election)中,英国保守党政府利用南非战争(1899—1902年)横扫了自由党对手;美帝国主义在1898年对西班牙的战争中成功动员了枪支的普及。事实上,以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1901—1909年任美国总统)为首的美国统治精英恰好发现,手持枪支的牛仔真正象征了美国精神、自由和本土白人的传统,可以抵御大举涌入的低阶层移民和无法控制的大城市。从那时起,这一象征被广泛利用。”关于1898年的美西战争,霍布斯鲍姆在没有提供证据或引文的情况下提出了若干因果论断。他声称,第一,统治精英(以罗斯福为首)动员了公众支持战争;第二,他们利用枪支和一场成功战争的印象完成了动员;第三,统治精英在帝国主义精神的驱使下宣战(他把“美帝国主义”拟人化,但在语境中又把它与统治精英联系起来)。所有这些主张都是解释偏差的经典案例。首先,在美西战争之前,罗斯福并没有领导统治精英。1898年的时候,他还没有担任纽约州州长,更没有成为美国总统;当时他是海军助理部长。在分析历史发展时,都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不确定性。确切地说,他是重要人物,但在外交政策上还没有话语权。倘若总统威廉•麦金莱得知自己的内阁下属官员被视为统治精英的“首脑”,一定会大吃一惊。历史学家习惯夸大西奥多•罗斯福在19世纪90年代的作用,因为(我们推测)他们对罗斯福总统任期和遗留问题的了解影响了他们对历史现实的评估。其次,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主要决策者(即麦金莱总统及其内阁)有意使用了枪支或成功战争的印象。相反,许多内阁成员反对战争,而麦金莱本人在宣战前也非常低调,显得犹豫不决。这是对未来结果的了解(以及也许是突出的牛仔形象)如何影响事件解释的又一案例。最后,美国在美西战争后成为帝国主义强国,这本身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是宣战的主要动机。我们认为,霍布斯鲍姆犯的这个错误同样是由于解释偏差造成的。他对未来帝国主义的认识影响了他对战前的推动力和态度的理解。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mpire:1875-1914(New York:Vintage Books,1989,第1版,1987),第103—104页。)他们往往会忽视生活在过去情境下的人们面对的未来有多么不确定。这样做的部分结果是,人们常常高估自己偏好的那些有关过去的解释,即他们对历史事件的因果论断(causal claims)。
有些未来事件并没有发生,但本来多半是会发生的,这种认知充分显现了上述高估问题。就像“9•11”委员会极富诗意的描述:“但事情发生的经过如此透亮,以至于其他一切都被置于更深的阴影之中……时间一天天过去,可以找到的文件日益增多,事件的真相也愈加清晰。然而,随着对过去世界的关注和不确定性逐渐消退,现在越发难以重新想象那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而对它的残余记忆也因后来发生的事情和流传的描述而受到歪曲、渲染。”(*1.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United States,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C.: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United States,2004),第339页。)在任何一段相对平淡的时间里,总有某些潜在的重大事件不曾发生。譬如,大家想想冷战期间美苏没有爆发任何重大的直接暴力冲突;自2001年之后,美国避免了由外国发动的重大恐怖事件。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对历史的书写就会截然不同,会更加强调背后的其他动因,而可能与我们的直觉相反的是,这些动因也存在于过去的现实中。
社会和政治运动同样对过分自信的因果论断提出质疑。这些运动的进程极不确定。想想过去十年里,同性婚姻出乎意料地被迅速接受,堕胎辩论持续白热化,民粹主义在全球兴起。对曾经高度不确定的结果所做的简单化解释,我们应持怀疑态度。
本文旨在探讨解释偏差现象,即历史叙事倾向于追溯一条明确的因果路径,而当时的预测则本应认识到众多的不确定性。(*1.当时的一些预测可能很有信心,即认为可能性极高,但和实际发生的情况相反,譬如上文提到的“阿拉伯之春”和苏联解体。关于预测和专家判断的更多信息,请参阅:Jeffrey A.Friedman,War and Chance:Assessing Uncertain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hilip E.Tetlock,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hilip E.Tetlock and Dan Gardner,Superforecasting:The Art and Science of Prediction(New York:Crown,2016);and Don A.Moore,“When Less Confidence Leads to Better Results,”New Yorker(25 November 2013),Available:https://www.newyorker.com/business/currency/when less confidence leads to better results.这些作品中都有一个令人沮丧的主题,即大多数预测者甚至是该领域的专家,都太过自信了。)解释偏差带有尴尬的副作用,诱使个人夸大历史影响的重要性,甚至扭曲历史的性质和事件本身。这会影响人们如何解读过去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政治学家中有一个诙谐的说法,即任何一个持有战争起因论的人都务必要用一战作为佐证。显然,一战那么复杂,完全能为几十种相互矛盾的战争理论提供依据。(*2.这里,我们并非暗示政治学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解释偏差的影响。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困扰着任何对历史做出因果论断的人。)
我们并不是说,解释偏差是历史学家或新闻播报员故意误导听众的伎俩;(*3.诚然,有些人确实是故意误导,但这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故意误导与完全透明和全面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在这个地带里,只选择支持论题的事实、叙述和数据也无疑是有益的。)也不是说,人们一遇到历史叙事就会变得稀里糊涂。相反,解释偏差是一种自然倾向,在某些时候几乎影响所有人,有些人甚至一直受到影响。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我们首先阐述解释偏差,证明它源于对不确定性的忽视。探讨这一概念后,我们将区分解释偏差与后视偏差(hindsight bias)等相关概念。接着,我们分析解释偏差最可能出现的原因和地方,以及如何克服它。最后,我们简要评述在历史分析中接受不确定性从而减少解释偏差的积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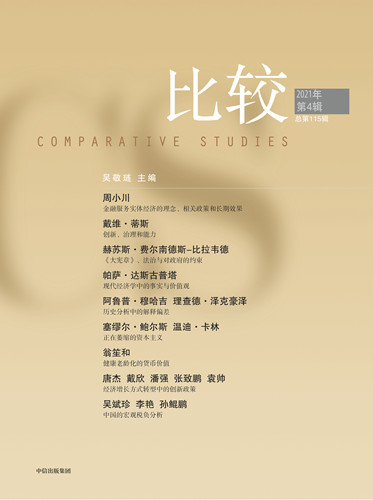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评论区 0
本篇文章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