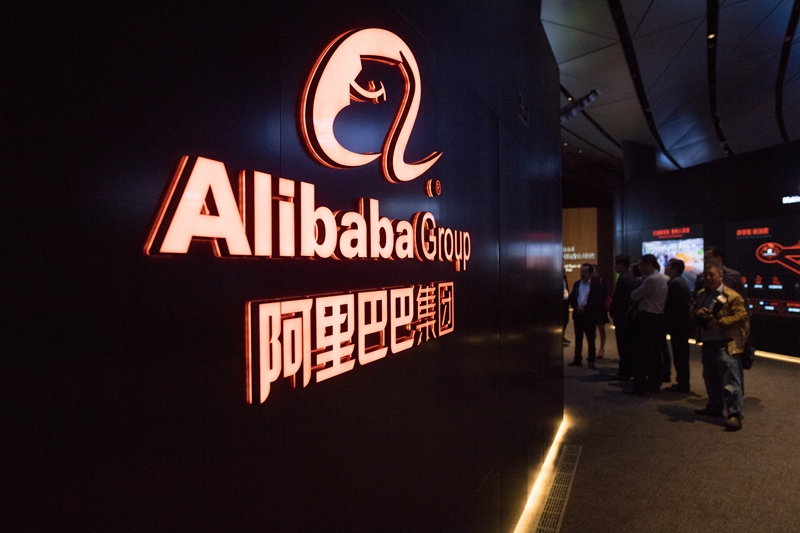*马歇尔·斯坦鲍姆 莫里斯·斯图克Marshall Steinbaum, 美国犹他大学经济学副教授;Maurice EStucke,美国田纳西大学法学院Douglas ABlaze杰出法学教授。原文“The Effective Competition Standard:A New Standard for Antitrust”发表于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第89期,第595—623页。
**作者感谢Peter Carstensen、Bert Foer、Gene Kimmelman、Jack Kirkwood、Ganesh Sitaraman、Sandeep Vaheesan、Spencer Weber Waller,以及2018年4月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21世纪反垄断会议”与会者的有益意见。
美国反垄断制度的失败,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当今的市场势力(market power)问题。宽松的反垄断法及其执法使企业合并等令人担忧的趋势不受质疑,进一步固化了扭曲的美国经济。在高度集中的市场里,个人的选择有限,几乎无权为自己需要的商品和服务选择价格、质量或供应商;工人面对强势的雇主,很少有机构能帮助他们货比三家、讨价还价,以获得有竞争力的工资和福利;而供应商只有向强大的中介机构付费或屈从于收购,才能进入市场。
我们的文章为法院提供了一个替代消费者福利标准的方案。消费者福利标准含糊不清且乏善可陈,只根据消费者面临的潜在后果来识别竞争受到的威胁,忽略了对工人、供应商、产品质量和创新的不利影响。
我们的有效竞争标准将恢复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即恢复经济中受到损害的竞争,包括整个供应链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这些改变可以分散私人权力,对保护美国的竞争性市场乃至个人和整体经济至关重要。
引言
正如法学者和经济学者日益注意到的,美国存在市场势力问题。新的证据表明,美国已经发生竞争减少、加价幅度提高、集中度增大、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加剧等现象。现行的竞争法以几乎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使少数人受益。
反垄断法应该处理经济权力集中的问题。但这套法律在两个方面遭到了挟持。首先,理论家们将反垄断的实质从应对多个目标,缩小到了只关注消费者福利的概念,即反垄断法意义上的竞争损害仅包括对消费者及其福利的损害,而这几乎完全由产出市场的价格和数量效应衡量。其次,一些法院和执法者甚至更进一步,拒绝认定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应负有反垄断责任,理由是这种行为会带来其他好处,比如长期经济增长。最近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包括俄亥俄诉美国运通公司案(*138 S Ct 2274(2018))和美国地方法院允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时代华纳合并案(**United States v AT&T Inc,310 F Supp 3d 161,253-54(DDC 2018),affd 916 F3d 1029(DC Cir 2019))的判决,无不演绎了在现行消费者福利标准下,反垄断法如何被削弱和扭曲至完全超越了所有人的认知。法院大大提高了政府和其他反垄断原告的举证责任,以至于《谢尔曼法案》(***26 Stat 209(1890),经《美国法典》第15编§§1-7修订。)和《克莱顿法案》(****38 Stat 730(1914),在第15编和第29编各节中做了修订。)对卡特尔以外的诸多反竞争行为都变成了不可执行。
如果美国继续对合并案进行“浅尝辄止”的反垄断审查,对主导企业滥用市场势力的行为视而不见,资本集中和裙带资本主义就有可能加剧,竞争和人们的福祉将进一步减少,权力和利润将继续落入更少数人手中。初创企业、中小企业以及作为工人、消费者和民主公民的更广泛的美国人,将任由少数强大而专横的公司摆布。
倘若我们恢复反垄断法保障有效竞争的作用,上述趋势便可逆转。为了解决当今的市场势力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有效竞争”的反垄断标准,以取代现行的消费者福利标准,对于后者,法院和学者总是做出各不相同(有时甚至毫不一致)的解释。有效竞争标准将恢复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将尾大不掉的私人权力分散至经济中任何可能的领域,包括整个供应链和劳动力市场。
反垄断并非可有可无。事实上,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经济权力的集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反垄断对经济结构都极其重要。虽然本文阐明反垄断政策旨在分散权力,但我们也认识到,单靠反垄断是无法实现这一紧迫目标的。累进税收、劳工改革、有效的(不被俘获的)特定部门监管、公司治理以及社会福利政策都是必要的政策工具。因此,尽管强有力的反垄断执法通常是保持竞争性市场结构的重要条件,但政策制定者不应局限于这类工具。
为理解制定有效竞争标准的必要性,首先从历史角度切入是有助益的。本文第1节描述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消费者福利标准的兴起,以及法院和机构在适用这一标准时遇到的操作困难。悖论的是,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消费者福利标准既无助于消费者,也无助于消费者的福利。相反,美国经济存在市场势力问题,在许多行业,少数企业收获了巨大的超竞争利润(supracompetitive profits)。
为了促进竞争和更具包容性的经济,第2节概述有效竞争标准;第3节阐明有效竞争标准下可能发生的反垄断解释、法律和执法方面的变化;第4节探讨可以实现这些变化的其他法律和政治手段。
1.20世纪70年代末消费者福利标准的兴起及其在应用中的操作困难
1987年,有一位学者指出,术语“效率”和“消费者福利”已经“成为反垄断话语中的主导词汇,但人们对它们的确切含义并没有达成明确的共识”,而且消费者福利是“现代反垄断分析中最被滥用的术语”。(*Joseph FBrodley,The Economic Goals of Antitrust:Efficiency,Consumer Welfare,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62 NYU L Rev 1020,1020,1032(1987)Also See Walter Adams and James WBrock,The Antitrust Vision and Its Revisionist Critics,35 NY L Sch L Rev 939,943-946(1990))今天,情况依然如此。
1975年以前,美国最高法院从未在反垄断案件中提及“消费者福利”一词。(**参见United States v Citizens & Southern National Bank,422 US 86,131 n 1(1975)(美国最高法院法官Brennan持异议)。)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崛起,情况有了变化,当时的罗伯特·博克教授更是于1978年出版了《反托拉斯悖论》一书。(***参见Robert Bork,The Antitrust Paradox:A Policy at War with Itself(Basic Books 1978)。)在过去40年里,受芝加哥学派影响的执法者认为反垄断的政治和道德理由不够严谨,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反垄断政策的真正目的,即提高经济效率;而芝加哥学派经常把经济效率和消费者福利混为一谈。(*参见Mark Glick,The Unsound Theory Behind the Consumer(and Total)Welfare Goal in Antitrust,63 Antitrust Bull 455,485-92(2018);Maurice EStucke,Reconsidering Antitrusts Goals,53 BC L Rev 551,563-66(2012)。)在他们看来,反垄断依赖的是一个不完整且扭曲的竞争概念。(**关于芝加哥学派竞争概念的描述,详见Richard APosner,The Chicago School of Antitrust Analysis,127 U Pa L Rev 925,931-33(1979)。关于某些批评,参见Amanda PReeves and Maurice EStucke,Behavioral Antitrust,86 Ind L J 1527,1548,1554-70(2011);Maurice EStucke,Better Competition Advocacy,82 St Johns L Rev 951,957,979-87(2008)。)
芝加哥学派认为,市场会自我修正,自由进入是侵蚀现存市场势力的“自然”条件。(***参见Stucke,82 St Johns L Rev at 957(引自注释9)。)这些重要的经济假设从未在反垄断经济学之内或之外占据上风,但它们仍然严重影响了非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和司法机构。这是因为哈佛学派有自己(多少沿袭前人)的理由质疑反垄断强力执法的有效性,即反垄断执法没有适当地针对道德或政治目标,而且反垄断干预对经济的有效运行可能弊大于利。(****参见William EKovacic,The Intellectual DNA of Modern USCompetition Law for Dominant Firm Conduct:The Chicago/Harvard Double Helix,2007 Colum Bus L Rev 1,17-33;William E.Kovacic,The Chicago Obsession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USAntitrust History,87 U Chi L Rev 459,464-66,478-82(2020)。)
因此,前人认为,不需要靠强有力的反垄断执法来创造或维持使竞争有效的必要条件。当代反垄断共识源于如下观点:市场力量可以自然地纠正市场势力的偶发案例,甚至可以比政府干预做得更好、更快。此外,干预性反垄断执法更有可能生成持久的市场势力,而不是削弱市场势力。(*****参见Frank HEasterbrook,The Limits of Antitrust,63 Tex L Rev 1,17-40(1984)。另见Bork,Antitrust Paradox at 406-07(引自注释7)。)考虑到未来的效率和创新前景,反垄断当局认为,电信(******参见Tim Wu,The Master Switch:The Rise and Fall of Information Empires,244-45(Knopf 2010)。)、金融(*******参见Simon Johnson and James Kwak,Thirteen Bankers:The Wall Street Takeoverand the Next Financial Meltdown 12,203(Pantheon 2010);Jesse WMarkham Jr,Lessons for Competition Law from the Economic Crisis:The Prospect for Antitrust Responses to the“TooBigtoFail”Phenomenon,16 Fordham J Corp & Fin L 261,291(2011)。)以及相关行业的集中化加剧了风险,但认为这对竞争的潜在损害可以受到控制,因为有利于竞争的“技术变革”会促成无处不在的自由进入的威胁。
在消费者福利标准下,卡特尔诉讼之外的反垄断执法活动有所减少。到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初,美国既没有大众化的反垄断运动,也没有多少引人注目的反垄断诉讼。(*Kovacic,87 U Chi L Rev at 479-80(引自注释11)。)例如,在过去20年,美国司法部仅根据《谢尔曼法案》第2条对微软提起过一次重大的垄断诉讼。(**参见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87 F Supp 2d 30,35(DDC 2000),部分同意,部分修订,253 F3d 34,118-19(DC Cir 2001)。另见Department of Justice,Antitrust Division Workload Statistics FY 2009-2018(July 1,2019),存档于https://permacc/F7DC-JDUE;Department of Justice,Antitrust Division Workload Statistics FY 2000-2009(Apr 4,2012),存档于https://permacc/2MTB-J8LU。)另外,尽管政府在一些指控上胜诉,但上诉法院还是趁机削弱了该法案的某些方面,加重了原告的程序负担。(***参见Microsoft,253F3d at 80-81,107。)微软的上诉判决,甚至美国司法部的裁决,都反映了一种深刻的矛盾心理,即反垄断到底能不能有效地构建市场,造福公众。(****参见Andrew IGavil and Harry First,The Microsoft Antitrust Cases: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16-31(MIT 2014)。)与过去20年的萧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0—1972年间司法部对卖方寡头垄断提起了39起民事诉讼和3起刑事诉讼。(*****Department of Justice,Antitrust Division Workload Statistics FY 1970-1979,存档于https://permacc/35CW-G5N9。)
正如我们在其他文章中阐述的(******参见Marshall ISteinbaum and Maurice EStucke,The Effective Competition Standard:A New Standard for Antitrust *11-21(Roosevelt Institute,Sept 2018),存档于https://permacc/AR68-6XKN。),消费者福利标准存在不少缺陷,包括:
在消费者福利标准下,竞争日益减少,这损害了消费者、工人和创新:倘若消费者福利在过去40年里确实增加了,消费者福利标准的缺陷就不会那么令人担忧。即使消费者福利增加了,也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在更好的反垄断标准下,他们的福利本可以增加更多一点,但这无非是程度的问题。遗憾的是,在消费者福利标准下,许多市场的竞争显著减弱。事实证明,消费者福利标准既无益于消费者,也无益于他们的福利。
消费者福利标准与上游滥用行为难以调和:该标准很难与明显的反竞争限制相协调,因为这些限制不影响消费者,却影响上游销售商和工人,比如禁止挖人协议(non-poaching agreement)。
没有公认的定义:消费者福利标准没有促进全球趋同。对全世界不同的竞争监管机构而言,这个标准并不相同。
法治问题:鉴于现有的消费者福利定义五花八门,法院根据自己的消费者福利概念得出不一致的裁决也就不足为奇了。消费者福利标准不是客观标准,而是有相当大的主观性,更确切地说,是对反竞争行为有相当大的容忍度。
因此,消费者福利标准作为一个反垄断目标几乎没有指导意义。对于这个术语的实际含义以及谁是消费者,人们尚未达成共识。根据目前的任何定义,始终“没有简单且无可争议的方法能量化消费者福利受到的损害,并适用于所有情况”。(*Competition Enforcement and Consumer Welfare:Setting the Agenda 47(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2011),存档于https://permacc/GH9U-CJQK。)更有甚者,在这个标准下,反垄断不是阻止而是助长了美国当前的市场势力问题。
反垄断应该在促进开放的竞争性市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今天的市场势力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最终会迎来更不稳定、效率更低的经济,面临增长、公共投资和机会日渐减少的逆境。(**参见Jonathan BBaker,The Antitrust Paradigm:Restoring a Competitive Economy(Harvard 2019)。)随着99%的人口被剥夺权力,选民对政府将更加失望和更不信任,进而削弱美国的民主。给社会造成的最大代价是“我们的认同感受到侵蚀,而在这种认同感中,公平竞争、机会平等和社会责任感何其重要”。(***Joseph EStiglitz,The Price of Inequality: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117(Norton 2012))
经济政策需要选择,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具有分配后果。美国大部分的经济不平等是有意而为之的法律和执法决策所致,而在过去40年里,政府没能保护99%的人。相反,有经济实力的人以牺牲社会为代价,利用政府发家致富。既然反垄断政策是解决市场势力问题的必要(但不充分)工具,那么现在是时候制定新的反垄断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