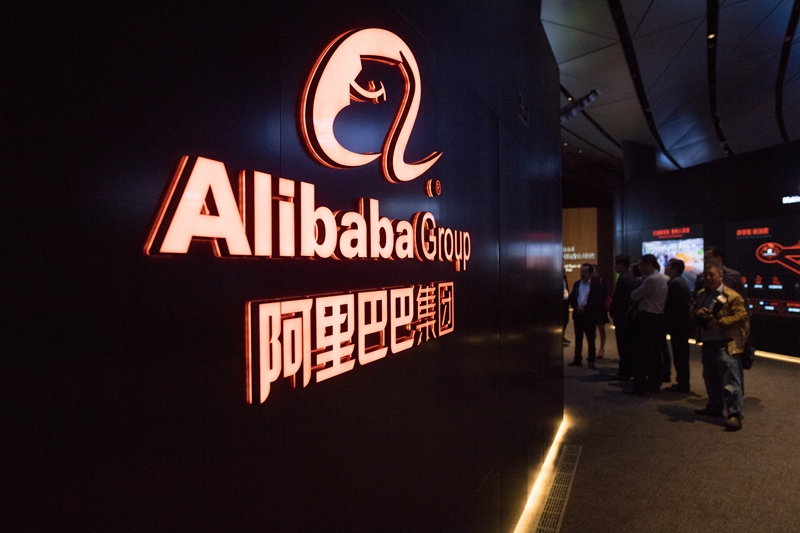*马歇尔·斯坦鲍姆 莫里斯·斯图克Marshall Steinbaum, 美国犹他大学经济学副教授;Maurice EStucke,美国田纳西大学法学院Douglas ABlaze杰出法学教授。原文“The Effective Competition Standard:A New Standard for Antitrust”发表于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第89期,第595—623页。
**作者感谢Peter Carstensen、Bert Foer、Gene Kimmelman、Jack Kirkwood、Ganesh Sitaraman、Sandeep Vaheesan、Spencer Weber Waller,以及2018年4月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21世纪反垄断会议”与会者的有益意见。
美国反垄断制度的失败,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当今的市场势力(market power)问题。宽松的反垄断法及其执法使企业合并等令人担忧的趋势不受质疑,进一步固化了扭曲的美国经济。在高度集中的市场里,个人的选择有限,几乎无权为自己需要的商品和服务选择价格、质量或供应商;工人面对强势的雇主,很少有机构能帮助他们货比三家、讨价还价,以获得有竞争力的工资和福利;而供应商只有向强大的中介机构付费或屈从于收购,才能进入市场。
我们的文章为法院提供了一个替代消费者福利标准的方案。消费者福利标准含糊不清且乏善可陈,只根据消费者面临的潜在后果来识别竞争受到的威胁,忽略了对工人、供应商、产品质量和创新的不利影响。
我们的有效竞争标准将恢复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即恢复经济中受到损害的竞争,包括整个供应链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这些改变可以分散私人权力,对保护美国的竞争性市场乃至个人和整体经济至关重要。
引言
正如法学者和经济学者日益注意到的,美国存在市场势力问题。新的证据表明,美国已经发生竞争减少、加价幅度提高、集中度增大、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加剧等现象。现行的竞争法以几乎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使少数人受益。
反垄断法应该处理经济权力集中的问题。但这套法律在两个方面遭到了挟持。首先,理论家们将反垄断的实质从应对多个目标,缩小到了只关注消费者福利的概念,即反垄断法意义上的竞争损害仅包括对消费者及其福利的损害,而这几乎完全由产出市场的价格和数量效应衡量。其次,一些法院和执法者甚至更进一步,拒绝认定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应负有反垄断责任,理由是这种行为会带来其他好处,比如长期经济增长。最近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包括俄亥俄诉美国运通公司案(*138 S Ct 2274(2018))和美国地方法院允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时代华纳合并案(**United States v AT&T Inc,310 F Supp 3d 161,253-54(DDC 2018),affd 916 F3d 1029(DC Cir 2019))的判决,无不演绎了在现行消费者福利标准下,反垄断法如何被削弱和扭曲至完全超越了所有人的认知。法院大大提高了政府和其他反垄断原告的举证责任,以至于《谢尔曼法案》(***26 Stat 209(1890),经《美国法典》第15编§§1-7修订。)和《克莱顿法案》(****38 Stat 730(1914),在第15编和第29编各节中做了修订。)对卡特尔以外的诸多反竞争行为都变成了不可执行。
如果美国继续对合并案进行“浅尝辄止”的反垄断审查,对主导企业滥用市场势力的行为视而不见,资本集中和裙带资本主义就有可能加剧,竞争和人们的福祉将进一步减少,权力和利润将继续落入更少数人手中。初创企业、中小企业以及作为工人、消费者和民主公民的更广泛的美国人,将任由少数强大而专横的公司摆布。
倘若我们恢复反垄断法保障有效竞争的作用,上述趋势便可逆转。为了解决当今的市场势力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有效竞争”的反垄断标准,以取代现行的消费者福利标准,对于后者,法院和学者总是做出各不相同(有时甚至毫不一致)的解释。有效竞争标准将恢复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将尾大不掉的私人权力分散至经济中任何可能的领域,包括整个供应链和劳动力市场。
反垄断并非可有可无。事实上,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经济权力的集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反垄断对经济结构都极其重要。虽然本文阐明反垄断政策旨在分散权力,但我们也认识到,单靠反垄断是无法实现这一紧迫目标的。累进税收、劳工改革、有效的(不被俘获的)特定部门监管、公司治理以及社会福利政策都是必要的政策工具。因此,尽管强有力的反垄断执法通常是保持竞争性市场结构的重要条件,但政策制定者不应局限于这类工具。
为理解制定有效竞争标准的必要性,首先从历史角度切入是有助益的。本文第1节描述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消费者福利标准的兴起,以及法院和机构在适用这一标准时遇到的操作困难。悖论的是,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消费者福利标准既无助于消费者,也无助于消费者的福利。相反,美国经济存在市场势力问题,在许多行业,少数企业收获了巨大的超竞争利润(supracompetitive profits)。
为了促进竞争和更具包容性的经济,第2节概述有效竞争标准;第3节阐明有效竞争标准下可能发生的反垄断解释、法律和执法方面的变化;第4节探讨可以实现这些变化的其他法律和政治手段。
1.20世纪70年代末消费者福利标准的兴起及其在应用中的操作困难
1987年,有一位学者指出,术语“效率”和“消费者福利”已经“成为反垄断话语中的主导词汇,但人们对它们的确切含义并没有达成明确的共识”,而且消费者福利是“现代反垄断分析中最被滥用的术语”。(*Joseph FBrodley,The Economic Goals of Antitrust:Efficiency,Consumer Welfare,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62 NYU L Rev 1020,1020,1032(1987)Also See Walter Adams and James WBrock,The Antitrust Vision and Its Revisionist Critics,35 NY L Sch L Rev 939,943-946(1990))今天,情况依然如此。
1975年以前,美国最高法院从未在反垄断案件中提及“消费者福利”一词。(**参见United States v Citizens & Southern National Bank,422 US 86,131 n 1(1975)(美国最高法院法官Brennan持异议)。)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崛起,情况有了变化,当时的罗伯特·博克教授更是于1978年出版了《反托拉斯悖论》一书。(***参见Robert Bork,The Antitrust Paradox:A Policy at War with Itself(Basic Books 1978)。)在过去40年里,受芝加哥学派影响的执法者认为反垄断的政治和道德理由不够严谨,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反垄断政策的真正目的,即提高经济效率;而芝加哥学派经常把经济效率和消费者福利混为一谈。(*参见Mark Glick,The Unsound Theory Behind the Consumer(and Total)Welfare Goal in Antitrust,63 Antitrust Bull 455,485-92(2018);Maurice EStucke,Reconsidering Antitrusts Goals,53 BC L Rev 551,563-66(2012)。)在他们看来,反垄断依赖的是一个不完整且扭曲的竞争概念。(**关于芝加哥学派竞争概念的描述,详见Richard APosner,The Chicago School of Antitrust Analysis,127 U Pa L Rev 925,931-33(1979)。关于某些批评,参见Amanda PReeves and Maurice EStucke,Behavioral Antitrust,86 Ind L J 1527,1548,1554-70(2011);Maurice EStucke,Better Competition Advocacy,82 St Johns L Rev 951,957,979-87(2008)。)
芝加哥学派认为,市场会自我修正,自由进入是侵蚀现存市场势力的“自然”条件。(***参见Stucke,82 St Johns L Rev at 957(引自注释9)。)这些重要的经济假设从未在反垄断经济学之内或之外占据上风,但它们仍然严重影响了非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和司法机构。这是因为哈佛学派有自己(多少沿袭前人)的理由质疑反垄断强力执法的有效性,即反垄断执法没有适当地针对道德或政治目标,而且反垄断干预对经济的有效运行可能弊大于利。(****参见William EKovacic,The Intellectual DNA of Modern USCompetition Law for Dominant Firm Conduct:The Chicago/Harvard Double Helix,2007 Colum Bus L Rev 1,17-33;William E.Kovacic,The Chicago Obsession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USAntitrust History,87 U Chi L Rev 459,464-66,478-82(2020)。)
因此,前人认为,不需要靠强有力的反垄断执法来创造或维持使竞争有效的必要条件。当代反垄断共识源于如下观点:市场力量可以自然地纠正市场势力的偶发案例,甚至可以比政府干预做得更好、更快。此外,干预性反垄断执法更有可能生成持久的市场势力,而不是削弱市场势力。(*****参见Frank HEasterbrook,The Limits of Antitrust,63 Tex L Rev 1,17-40(1984)。另见Bork,Antitrust Paradox at 406-07(引自注释7)。)考虑到未来的效率和创新前景,反垄断当局认为,电信(******参见Tim Wu,The Master Switch:The Rise and Fall of Information Empires,244-45(Knopf 2010)。)、金融(*******参见Simon Johnson and James Kwak,Thirteen Bankers:The Wall Street Takeoverand the Next Financial Meltdown 12,203(Pantheon 2010);Jesse WMarkham Jr,Lessons for Competition Law from the Economic Crisis:The Prospect for Antitrust Responses to the“TooBigtoFail”Phenomenon,16 Fordham J Corp & Fin L 261,291(2011)。)以及相关行业的集中化加剧了风险,但认为这对竞争的潜在损害可以受到控制,因为有利于竞争的“技术变革”会促成无处不在的自由进入的威胁。
在消费者福利标准下,卡特尔诉讼之外的反垄断执法活动有所减少。到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初,美国既没有大众化的反垄断运动,也没有多少引人注目的反垄断诉讼。(*Kovacic,87 U Chi L Rev at 479-80(引自注释11)。)例如,在过去20年,美国司法部仅根据《谢尔曼法案》第2条对微软提起过一次重大的垄断诉讼。(**参见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87 F Supp 2d 30,35(DDC 2000),部分同意,部分修订,253 F3d 34,118-19(DC Cir 2001)。另见Department of Justice,Antitrust Division Workload Statistics FY 2009-2018(July 1,2019),存档于https://permacc/F7DC-JDUE;Department of Justice,Antitrust Division Workload Statistics FY 2000-2009(Apr 4,2012),存档于https://permacc/2MTB-J8LU。)另外,尽管政府在一些指控上胜诉,但上诉法院还是趁机削弱了该法案的某些方面,加重了原告的程序负担。(***参见Microsoft,253F3d at 80-81,107。)微软的上诉判决,甚至美国司法部的裁决,都反映了一种深刻的矛盾心理,即反垄断到底能不能有效地构建市场,造福公众。(****参见Andrew IGavil and Harry First,The Microsoft Antitrust Cases: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16-31(MIT 2014)。)与过去20年的萧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0—1972年间司法部对卖方寡头垄断提起了39起民事诉讼和3起刑事诉讼。(*****Department of Justice,Antitrust Division Workload Statistics FY 1970-1979,存档于https://permacc/35CW-G5N9。)
正如我们在其他文章中阐述的(******参见Marshall ISteinbaum and Maurice EStucke,The Effective Competition Standard:A New Standard for Antitrust *11-21(Roosevelt Institute,Sept 2018),存档于https://permacc/AR68-6XKN。),消费者福利标准存在不少缺陷,包括:
在消费者福利标准下,竞争日益减少,这损害了消费者、工人和创新:倘若消费者福利在过去40年里确实增加了,消费者福利标准的缺陷就不会那么令人担忧。即使消费者福利增加了,也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在更好的反垄断标准下,他们的福利本可以增加更多一点,但这无非是程度的问题。遗憾的是,在消费者福利标准下,许多市场的竞争显著减弱。事实证明,消费者福利标准既无益于消费者,也无益于他们的福利。
消费者福利标准与上游滥用行为难以调和:该标准很难与明显的反竞争限制相协调,因为这些限制不影响消费者,却影响上游销售商和工人,比如禁止挖人协议(non-poaching agreement)。
没有公认的定义:消费者福利标准没有促进全球趋同。对全世界不同的竞争监管机构而言,这个标准并不相同。
法治问题:鉴于现有的消费者福利定义五花八门,法院根据自己的消费者福利概念得出不一致的裁决也就不足为奇了。消费者福利标准不是客观标准,而是有相当大的主观性,更确切地说,是对反竞争行为有相当大的容忍度。
因此,消费者福利标准作为一个反垄断目标几乎没有指导意义。对于这个术语的实际含义以及谁是消费者,人们尚未达成共识。根据目前的任何定义,始终“没有简单且无可争议的方法能量化消费者福利受到的损害,并适用于所有情况”。(*Competition Enforcement and Consumer Welfare:Setting the Agenda 47(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2011),存档于https://permacc/GH9U-CJQK。)更有甚者,在这个标准下,反垄断不是阻止而是助长了美国当前的市场势力问题。
反垄断应该在促进开放的竞争性市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今天的市场势力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最终会迎来更不稳定、效率更低的经济,面临增长、公共投资和机会日渐减少的逆境。(**参见Jonathan BBaker,The Antitrust Paradigm:Restoring a Competitive Economy(Harvard 2019)。)随着99%的人口被剥夺权力,选民对政府将更加失望和更不信任,进而削弱美国的民主。给社会造成的最大代价是“我们的认同感受到侵蚀,而在这种认同感中,公平竞争、机会平等和社会责任感何其重要”。(***Joseph EStiglitz,The Price of Inequality: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117(Norton 2012))
经济政策需要选择,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具有分配后果。美国大部分的经济不平等是有意而为之的法律和执法决策所致,而在过去40年里,政府没能保护99%的人。相反,有经济实力的人以牺牲社会为代价,利用政府发家致富。既然反垄断政策是解决市场势力问题的必要(但不充分)工具,那么现在是时候制定新的反垄断标准了。
2.有效竞争标准
从历史上看,反垄断从来不是为了提高分配效率或消费者福利。相反,反垄断旨在通过保护竞争过程分散私人权力。例如参见Barak Orbach,How Antitrust Lost Its Goal,81 Fordham L Rev2253,2256(2013)。
毋庸置疑,促进有效竞争过程的目标有其自身的瑕疵。它只是将辩论转移到一个尚待解决的更大问题上,即定义有效的竞争过程。缺失这样的定义,反垄断将沦为同义反复:竞争法的目标是“通过阻止反竞争行为促进竞争”。Consumer Unity & Trust Society Centre for Competition,Investment and Economic Regulation,Towards a Healthy Competition Culture(2003),存档于https://permacc/W89G-5RWK。
因此,为了给法院和反垄断机构提供更好的指导,我们首先提出以下有效竞争标准:
反垄断机构和法院应当以维护竞争性市场结构作为联邦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从而保护个人、购买者、消费者和生产者;给竞争者保留机会;促进个人自治(individual autonomy),提升个人福祉;以及分散私人权力。
让我们逐一解析各个要素:
维护竞争性市场结构:这就是承认竞争既非一种自然状态,也无法通过关注消费者剩余确保竞争。鉴于当前反垄断制度的失败在于太过轻信横向和纵向合并的表面好处,所以对这些合并应持怀疑态度。
保护个人、购买者、消费者和生产者:反垄断法既保护供应链本身的弹性,也保护整个供应链的市场参与者,包括个人、消费者、工人和上游供应商。
给竞争者保留机会:一个基本的价值观是,在供应链的各个层面都要有竞争,使上游企业能够进入市场而不受具有纵向合并潜力的强大中间商的强迫、干扰、排斥或歧视。
促进个人自治,提升个人福祉:历史上,法院一直把反垄断法奉为“自由企业的大宪章”,并认为它“对维护经济自由和我们的自由企业制度很重要,正如《权利法案》对保护我们的基本个人自由很重要”。(***United States v Topco Associates,Inc,405 US 596,610(1972))竞争政策可以促进包容性经济,从而推动自主性和整体福祉等重要的价值观。(****参见Maurice EStucke,Should Competition Policy Promote Happiness?81 Fordham L Rev 2575(2013)。)这对于买方权力尤其重要,特别是当这种权力在劳动力市场上行使时。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大法官曾经写道:“如果人们在产业上依赖他人的武断意志,那就没有自由。”(*Tim Wu,The Curse of Bigness:Antitrust in the New Gilded Age 40(Columbia Global Reports 2018))《克莱顿法案》说“劳动不是商品”,正反映了这种智慧。(**参见Clayton Act§6,38 Stat at 731,编入15 USC§17(“人的劳动不是商品”)。)大多数人依靠自身的劳动谋生。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单个工人的供给是高度缺乏弹性的。因此,工人往往会受到强大雇主的胁迫。防止这种胁迫本身就是目的。
分散私人权力:经济权力常常转化为政治权力,这不仅体现在正式的政治制度中,也体现在雇主和工人之间、集中化的买方和分散化的供应商之间的日常关系中,还体现在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输和引导的信息流动中。反垄断的基本目的是防止经济权力的集中产生反竞争、反民主的压力,并确保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包括在整个供应链和企业内部,实现包容、公平的权力分配。(***例如参见Tim Wu,The Curse of Bigness,54-58(引自注28)(讨论了行业越集中,可以预期政治进程越腐败);Robert Pitofsky,The Political Content of Antitrust,127 U Pa L Rev 1051,1051-52(1979)(“在解释反垄断法时排除某些政治价值观,这是糟糕的历史、糟糕的政策和糟糕的法律”,任何排除这些政治价值观的反垄断政策“都将对国会的意愿无动于衷”);Louis BSchwartz,“Justice”and Other NonEconomic Goals of Antitrust,127 U Pa L Rev 1076,1076(1979)(“假定的经济利益不应成为解决反垄断争议的唯一因素或决定性因素”)。)由于自由市场在我们的法律、伦理、道德、政治和社会框架内(而非外部)运行,所以,如果设计和维护得当,竞争过程将既限制股东和管理者剥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能力,又防止既有弱势群体被排除在经济之外或被边缘化。
3.有效竞争标准如何改变现状
有效竞争标准不同于消费者福利标准和总体福利标准(****现在,总体福利标准基本上已被弃用,该标准只关心经济效率,对消费者和销售者之间如何分配剩余没有任何立场。更具体地说,它只把反垄断对竞争的损害归结为负产出效应,并不把价格上涨视为竞争受到损害的证据。),它明确地脱离了作为反垄断分析基础的单一市场的局部均衡分析。有效竞争标准在四个重要方面与消费者福利标准有进一步的区别:
第一,只要大幅度减少竞争就足以承担法律责任。执法者和法院不必证明竞争减少如何损害消费者,也不必平衡一组利益相关者受到的伤害与另一组利益相关者的假定收益。(*在销售方面,证明消费者受到损害往往很困难,特别是对中间商品而言。证明买方权力对最终消费者有负面影响,则问题更大、难度更高。在实际应用时,消费者福利审查给出的是残缺且失真的消费者损害衡量标准。反垄断执法者通常会考虑涉嫌垄断行为对价格的直接影响。如果零售价格保持不变(或下降),那么竞争监管部门可能会根据消费者损害审查得出结论,认为涉嫌垄断的做法是竞争中性的或有利于竞争的。他们既不会深入调查关于买方权力的投诉,还可能认为任何非价格问题微不足道或者是推测性的。这暴露了测量消费者福利时的一个根本困难。买方权力会间接损害消费者。上游卖方也是消费者,比如没有多少钱购买商品的农民。当负外部性增加时,例如利润更低的农民通过增加污染、从事可持续性较差的农业、容忍更危险的工作场所或雇用未成年工人等方式投机取巧,我们的福利就会进一步减少。竞争监管部门一般不会考虑这些更难以量化的损害,但这些损害可能会超过价格下降带来的短期收益。监管部门缺乏工具评估买方权力造成的短期和长期损害(例如,多样性和创新减少)。因此,如果垄断压低了当地社区的工资,反过来又增加了纳税人的成本,这会不会被纳入竞争监管部门的消费者福利审查项目?几乎不会。)就此而言,有效竞争标准使反垄断更可执行。
第二,它认识到竞争需要竞争者。所以,它对垄断性、掠夺性和排他性的做法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这些做法往往会减少进入者和竞争者的竞争机会。
第三,不同于消费者福利标准只考虑对消费者的影响,有效竞争标准保护整个供应链中的市场参与者,包括工人和销售商。
最后,有效竞争标准取消了竞争减少将如何损害消费者福利这一不可靠的判断依据,从而恢复了《克莱顿法案》的宗旨,即“在贸易限制开始并发展成违反《谢尔曼法案》的全面限制之前制止贸易限制”。正如国会指出的:“与竞争损害的确定性和真实性相关的要求,与任何通过达成初期限制来补充《谢尔曼法案》的努力毫不相符。”(**Brown Shoe Co v United States,370 US 294,323 n 39(1962),quoting S Rep No 1775,81st Cong,2d Sess 6(1950),再版于1950年,USCCAN 4293,4298。)
为了在高度集中的市场中促进竞争和创新,有效竞争标准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背离当今宽松的反垄断政策。
3.1建立一套更清晰的新指标衡量企业是否具有市场势力
这一标准将首先推翻最高法院在美国运通案中对间接证据的不合理要求。(***参见American Express,138 S Ct at 2284,2290。)政府原告辩称,他们无须界定相关市场,因为他们有实际证据证明竞争受到了不利影响,即商户费用大增。最高法院表示反对,认定原告引用的案例涉及横向限制。最高法院认为,“纵向限制通常不会对竞争构成风险,除非施加这些限制的实体具有市场势力,而除非法院首先界定相关市场,否则无法对市场势力进行评估”。(*同上,2285 n 7。)
不言而喻的是,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证据证明市场势力。因此,要求握有市场势力直接证据的原告用间接证据证明市场势力,这实在毫无意义。试想,要求掌握连环杀手犯罪直接证据的检察官提供间接证据,这不荒唐吗?
由于最高法院最近在涉及纵向限制的案件中提出了令人费解的要求,原告将不得不界定相关市场(这通常是一项费钱又耗时的工作,要使用以价格为中心的反垄断工具),计算被告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然后证明该市场份额高到足以推断被告拥有市场势力,哪怕原告有确凿证据证明该限制具有反竞争效应。
法院不是为衡量市场势力建立标准(即反垄断市场的高市场份额),而是允许提供有关市场势力的直接和间接证据。正如众多学者论证的,高市场份额并非支持或反对市场势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有必要建立更广泛的指标。实际上,经济证据表明,即使市场份额较低的公司,有时也可以在上游对供应商和工人动用其显著的市场势力。(**例如参见Peter CCarstensen,Competition Policy and the Control of Buyer Power:A Global Issue,65-78(Edward Elgar 2017);Maurice EStucke,Looking at the Monopsony in the Mirror,62 Emory L J 1509,1533-40(2013)。)这些市场势力指标包括:
是否有能力单方面设定价格或工资,收取超出竞争水平的价格或支付低于工人边际生产率的工资;
是否有能力将不利的非价格合同条款强加给交易对手或根据自己的利益修改合同条款,包括将质量、隐私、创新或品种降低到竞争水平以下;
是否有能力排挤竞争者或进入者;
是否有能力单方面限制产出或就业;
是否有能力实施价格歧视或工资歧视;(*在Illinois Tool Works Inc诉 Independent Ink,Inc,547 US 28(2006)中,最高法院指出,价格歧视“可以提供市场势力的证据”,但“人们普遍认为,价格歧视也发生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同上,第44—45页。虽然法院特别援引了William JBaumol and Daniel GSwanson,The New Economy and Ubiquitous Competitive Price Discrimination:Identifying Defensible Criteria of Market Power,70 Antitrust L J 661,666(2003),但事实上,这两位作者是通过市场分割(即消费者之间无法交易)假设市场势力的。同上,见681 n 38。法院还援引了William MLandes and Richard APosner,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374-75(Belknap,2003),但Posner在其他文章中指出,“持续的价格歧视可能是垄断的证据,因为这与竞争性市场相悖”,Richard APosner,Antitrust Law 80(Chicago 2d ed 2001)。我们的观点很简单,即价格歧视就是市场势力的证据,虽然它本身可能是剥削性的,也可能是良性的。)
是否有能力长时间内赚取利润或向股东支付超过公司资本成本的款项。
在有效竞争标准下,原告可以使用以上任何一项来确定市场势力。
3.2更新卖方或买方垄断政策,加强《谢尔曼法案》第2条的执法力度
在最高法院现行的消费者福利标准下,垄断企业大可不必战战兢兢,因为最高法院已经显著减轻了它们对反竞争行为的潜在责任。掠夺性定价案件几乎销声匿迹。(**例如,美国司法部1999年提起了最后一宗掠夺案,但最终败诉。参见United States诉 AMR Corp,335 F3d 1109,1121(10th Cir 2003)。)现在,法院认为垄断者没有必须交易的义务。对于所有这些反竞争行为,法院务必接受“效率”辩护,就好像其他非法行为,譬如欺诈,可以通过某种更大的社会利益得到纠正一样,而这种标准在其他法律领域根本是不存在的。(***参见Microsoft,253 F3d at 59,77;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10(Aug 19,2010),存档于https://permacc/B3RM-WGMN。)
有效竞争标准将纠正最高法院根据《谢尔曼法案》第2条制定的经济决策的若干缺陷,如果要扭转而不仅仅是缓解经济中日益加剧的市场势力问题,这一点就势在必行。在有效竞争标准下,卖方垄断和买方垄断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对拥有强大市场势力的企业实施比默认情况下更严格的竞争政策。
根据有效竞争标准,在下列情况下,被告的单方面反竞争行为将违反《谢尔曼法案》:
首先,根据之前列出的一项或多项指标,被告拥有并动用强大的市场势力;
其次,这种市场势力排除了某些潜在的竞争和(或)限制,或者限制了一些实际的竞争;
最后,这种市场势力并非完全归因于被告的能力、规模经济、研发或自然优势。
接下来,作为简化对单方面行为执法的一部分,有效竞争标准要求将某些行为推定为违反《谢尔曼法案》第2条规定,包括:
有助于企业取得或维持卖方垄断或买方垄断势力的其他非法行为;
长期低于边际成本的掠夺性定价,目的是排挤竞争对手并保护市场势力,无须原告证明“损失补偿”;(*这一标准或将促进国际间更大程度的趋同。例如参见AKZO Chemie BV诉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ECR I-3359,3454-56(EU Just 1991)(如果主导企业以低于平均可变成本的价格淘汰竞争对手,则推定为违法;如果主导企业的定价介于总成本和平均可变成本之间,则可能是滥用,有证据表明存在反竞争意图)。)
用更简单的标准评估拒绝交易(**决定拒绝交易何时属于反竞争行为的标准可包括:
主导企业控制着开展特定业务必需的产品、服务、资源或设施;
拒绝交易可能会严重排斥竞争;
拒绝交易会阻止有潜在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出现,或者会阻止在相关市场改进现有产品;
主导企业无法以特定事实客观地证明其拒绝交易的正当性。
我们的建议将在主导企业何时有义务进行交易的问题上促进与欧盟法律更大的趋同。可参见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Guidance on the Commissions Enforcement Priorities in Applying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to Abusive Exclusionary Conduct by Dominant Undertakings(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Feb 2009),存档于https://permacc/E27MCGM8。这已经成为数字经济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例如参见Mark RWarner,Potential Policy Proposals for Regulation of Social Media and Technology Firms*21-23(白皮书草案),存档于https://permacc/S4EAA67K[讨论互用性(interoperability)的必要以及基础设施的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性(FRAND)条款]。)和排他性交易(***主导企业对其他公司自由竞争的任何重大限制通常都需要有合法的理由。这种方法将允许订立促进竞争的合同和其他限制。这项新标准与美国以外竞争法的发展相一致,将可阻止主导企业或技术平台从事排他行为,这种排他行为极可能会排斥竞争对手,削弱竞争。)何时违法,包括侵犯供应商的市场准入权;
“低成本排挤”(cheap exclusion),即主导企业采取低成本的行为以排斥、削弱或歧视其市场内的竞争对手,且这种行为并不提高效率。(*可参见Susan ACreighton,et al,Cheap Exclusion,72 Antitrust L J 975,980-82(2005)。)
为了明确企业实施价格歧视时需要考虑的一系列损害,我们还建议修改《克莱顿法案》第2条,以禁止伤害消费者、工人或其他市场参与者的价格歧视,譬如当企业追踪个人的消费模式、收集个人数据,然后以他们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或愿意工作的最低工资)促使他们购买原本不想要的东西。(**可参见John BKirkwood,Reforming the Robinson-Patman Act to Serve Consumers and Control Po-
werful Buyers,60 Antitrust Bull 358,359-61,374-75(2015)。见15 USC§13。)或者,国会可以考虑从一开始就限制客户数据收集。
3.3《克莱顿法案》第7条下的合并政策
通常,反垄断法的目的首先是防止形成有害的市场势力积聚。然而,根据当前的合并政策,执法者有责任证明企业合并可能会减少竞争(即通过提高价格),从而导致合并审查松懈,大规模收购不受挑战。为了纠正合并审查程序,我们建议对《克莱顿法案》第7条做以下修订(***参见15 USC§18。):
与其把责任加于原告,不如把责任转移给寻求的合并(1)显著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发起方,或者(2)让已经拥有显著市场势力(见前述指标所示)的企业承担。合并各方必须证明其拟议的收购不会实质性削弱竞争,不会形成卖方垄断或买方垄断,也不会帮助维持其市场势力。(****我们的建议并没有设定收购显著提高集中度的基准。一个原因是,在评估上游和下游效应时,阈值或标准可能会不同,毕竟买方垄断并非卖方垄断的镜像。另一个原因是,合适的阈值可能会低于2010年《合并指南》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阈值。John Kwoka教授的数据基于对合并后评估的研究,表明应将HHI阈值从2010年《合并指南》的当前水平下调,并根据主要剩余竞争对手的数量创建单独的阈值。因此,完全可以将HHI阈值恢复到较早的水平(或不高于2000年的水平),而主要剩余竞争对手的数量不低于5个。但正如Kwoka承认的,他的数据集只涉及经过合并后评估的行业。鉴于最近的经济研究探讨了企业动用市场势力的程度,可能需要另外的HHI阈值或剩余竞争对手的阈值。John Kwoka,Reviving Merger Control:A Comprehensive Plan for Reforming Policy and Practice 33-37(Antitrust Institute Working Paper,Oct 2018),存档于https://permacc/JC62-WTAA。)这将阻止卖方垄断者或买方垄断者收购新生的竞争对手,而这种收购既维护了垄断者的市场势力,还可能阻碍创新。
法院应考虑合并的所有潜在竞争结果:不仅要考虑消费者面对的价格,还要考虑合并对质量、选择、创新和隐私的损害等非价格影响。反垄断机构和法院应审查合并对工人和供应商的上游效应,以及对可能受到损害的消费者和其他人的下游效应,并且不能假定上游动用市场势力会给下游带来“效率”或者其损害可以由这些效率抵消。(*可以说,竞争监管机构应该已经根据《克莱顿法案》和自己的《合并指南》做出了相关考虑。参见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at§1(特别指出,“市场势力的增强也可以表现为对消费者产生不利影响的非价格条款和条件,包括产品质量降低、产品种类减少、服务缩减或创新乏力”);同上,参见§12(指出,反垄断机构如何考虑合并是否可能增强买方的市场势力,引自注释39)。尽管如此,这些机构通常会关注合并对下游价格的影响。因此,有学者建议,任何对合并的竞争分析都应包括上游效应。参见Carstensen,Competition Policy at 94-96(引自注释36)。这包括确定受合并影响的各种劳动力市场,以及评估合并对这些劳动力市场集中度的影响。例如参见Alan BKrueger and Eric APosner,Policy Proposal:A Proposal for Protecting LowIncome Workers from Monopsony and Collusion 12(Hamilton Project,2018),存档于https://permacc/6XSL-43NL。这包括计算合并前后这些劳动力市场的HHI水平,并确认“如果合并后绝对集中度和(或)HHI上升表明压低工资的风险太高,则推定反对合并。”同上。)
当纵向合并有可能提高企业扭曲竞争的能力和动机时,国会应予以禁止。
3.4《谢尔曼法案》第1条下的协议
国会应根据《谢尔曼法案》第1条修订相关法律,规范有关各方之间的协议,包括纵向限制,如转售价格维持、地域和其他非价格限制,以及非竞争条款和劳动合同中限制工人权利的其他规定。(**见15 USC§1。)这应该包括:
明确联邦反垄断法涵盖并平等保护品牌之间和品牌内部的竞争,即供应商-经销商网络内部和之间的竞争,如特许经营权;(***例如,在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Inc诉PSKS,Inc,551 US 877(2007)一案中,法院认为,反垄断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品牌间竞争,从而证明减少品牌内竞争是正当合理的。同上,第890页。但这一政策声明绝非出自《谢尔曼法案》或其立法史。它来自Continental TV,Inc诉GTE Sylvania Inc,433 US 36(1977)案中的一个脚注,其中法院指出,“品牌间竞争是相同的非商标产品(generic product,在本案中为电视机)制造商之间的竞争,是反垄断法的主要关注点。”同上,第52页,注释19。虽然这对非商标产品是正确的,但对品牌差异化商品并非如此。尝试用奥迪或奔驰的价格为宝马争取更好的价格(品牌间竞争),不同于用其他经销商提供的同一款宝马的价格进行谈判(品牌内竞争)。Leegin案之后,最新的经济调查结果“符合一种观点,即转售价格维持的反竞争解释往往压倒支持竞争的解释”。Baker,Antitrust Paradigm,第89页(引自注释22)。有效竞争标准可得出不利于价格和非价格纵向限制的有力推定。)
规定价格和非价格纵向限制是非法的,包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此类限制;除非在任何当事方都没有市场势力,且限制对促进创新和竞争是必要的情况下;(*例如参见Leegin,551 US at 913(Breyer持异议)(指出了法院确定转售价格维持的两个潜在好处:有利于进入和遏制搭便车)。因此,与本身违法的标准不同,我们建议的有效竞争标准将允许在不太可能破坏品牌内竞争的情况下进行纵向限制。另见John BKirkwood,Rethinking Antitrust Policy Toward RPM,55 Antitrust Bull 423,459-70(2010)(提出将非法行为的推定与安全港相结合,替代合理原则)。这里的安全港是指法律解释和适用的一项规则。当法律规定的措辞过于宽泛时,当事人只需采用某种适当的方式遵守法律就应被视为已经履行了法律义务。例如,在税法中,只要当事人尽了自己的努力以遵守法律,而这种努力可以某种可识别的形式表现出来,就不会被认为违法。——编者注)
进一步明确除了非法行为本身,企图从事非法行为(如串谋)的尝试也应被禁止。(**联邦贸易委员会可以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第5条对串谋邀请提出质疑。参见15 USC§45。司法部起诉此类企图的主要机制是根据《谢尔曼法案》第2条提出的企图垄断主张,这一点更难证明。因此,司法部提起的串谋邀请案件较少。著名案例之一,见United States诉American Airlines,Inc,743 F2d 1114(5th Cir 1984)案。)
3.5调整法院和执法者的方向,更多地关注上游
美国的反垄断法旨在保护卖方和工人。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司法部2016年宣布,打算对“雇主之间公然签署与更大的合法合作无关或不必要的禁止挖人协议和固定工资协议展开刑事调查”。(***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的Guidance for Human Resource Professionals on How Antitrust Law Applies to Employee Hiring and Compensation(Oct 20,2016),存档于https://permacc/23YX-HRMA。)该机构与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一致认定,工人和其他卖方一样,有权享受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好处。(****同上。)遗憾的是,司法部最近在介入特许经营合同中的禁止挖人条款的私人诉讼时,明显偏离了这一立场。(*****参见Marshall Steinbaum,Antitrust,the Gig Economy,and Labor Market Power,82 L & Contemp Probs 45,第51—52页(2019)。)
在关注上游时,执法者和法院不应假定买方垄断是卖方垄断的镜像。(******参见Stucke,62 Emory L J 1509(引自注释36)。)在Weyerhaeuser Co诉Ross Simmons Hardwood Lumber Co这一著名垄断案中,(*******549 US 312(2007)。)法院一开始就假定卖方垄断势力和买方垄断势力在经济学上是相似的,并有着紧密的理论联系。(*同上,第321—322页。另见Todd诉Exxon Corp,275 F3d 191,202(2d Cir 2001)(指出“由于衡量买方市场势力的方程式是衡量卖方市场势力的方程式的镜像……所以替代买家的数量越大,相关买家的市场势力就越小”);Growers 1-7诉 Ocean Spray Cranberries,Inc,2015 WL 13649090,4(D Mass);GMA Cover Corp诉 Saab Barracuda LLC,2012 WL 642739,6(ED Mich),2012年由WL 639528(ED Mich)通过;Sprint Nextel Corp诉AT&T Inc,821 F Supp 2d 308,324(DDC 2011);In re Southeastern Milk Antitrust Litigation,801 F Supp 2d 705,724(ED Tenn 2011);Addamax Corp诉 Open Software Foundation Inc,888 F Supp 274,280 n 9(D Mass 1995);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Department of Justice,Improving Health Care:A Dose of Competition ch 6,13(2004)(Health Report),存档于https://permacc/7BK8-XJZZ。)鉴于“卖方垄断势力与买方垄断势力之间的亲缘关系”,最高法院建议“类似的法律标准应适用于”卖方垄断和买方垄断的诉讼请求。(**Weyerhaeuser,549 US,第322页。)但是,对评估买方垄断的诉讼请求制定相关法律标准比简单地复制卖方垄断的标准要复杂得多。
卖方垄断和买方垄断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推断其拥有显著市场势力所需的市场份额。在审查卖方垄断的诉讼请求时,法院通常要求被告占有的市场份额非常大,往往达到70%或以上。(***参见United States诉Aluminum Co of America,148 F2d 416,424(2d Cir 1945)(认为“值得怀疑60%或64%”是否足够,“而33%肯定是不够的”);Southeastern Milk,801 F Supp 2d at 725[指出在Byars诉 Bluff City News Co,609 F2d 843,850(6th Cir 1979)一案中,裁定“75%—80%或更高比例是评估垄断势力的‘起点’”];RJReynolds Tobacco Co诉Philip Morris Inc,199 F Supp 2d 362,394(MD NC 2002)(“70%—75%通常被认为是支持垄断势力认定必需的最低市场份额”),affd RJ Reynolds Tobacco Co诉 Philip Morris USA,Inc,67 F Appx 810(4th Cir 2003)。)某个地区法院曾根据《谢尔曼法案》第2条驳回了一次诉讼请求,理由是约40%的市场份额并未达到“证实卖方垄断或买方垄断势力所需的阈值”。(****Southeastern Milk,801 F Supp 2d at 727。另见Lima LS PLC诉 PHL Variable Insurance Co,2013 WL 12286066,*1 n1(D Conn)(“衡量买方市场势力的方程式是衡量卖方市场势力的方程式的镜像”)。)
另一方面,拥有20%市场份额的零售商可以享有明显大于销售商的买方市场势力。(*****参见Carstensen,Competition Policy at 58(引自注释36);Toys“R”Us,Inc诉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221 F3d 928,937(7th Cir 2000)。21W2222332Q323 U122123。)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都认识到,“理论上,要为这类买方垄断问题设定市场份额阈值”十分困难。(******Health Reportat ch 6,*17(引自注释57)。)这些机构并没有仅仅依靠市场份额阈值确定买方垄断的市场势力,而是正确地鼓励法院考虑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1)买方占有的较大市场份额;(2)投入品市场中向上倾斜或有些缺乏弹性的供给曲线;(3)新买方无法或不愿进入市场,抑或当前买方无法或不愿扩大其市场份额。(*同前。)
因此,在有效竞争标准下,法院和竞争监管机构可以突破上游市场份额阈值的框框,减少误报的风险。甚至在恰当界定的市场上,市场份额较低的买方有时也能动用其巨大的市场势力。在决定何时、是否、向谁购买易腐产品以及购买多少该产品的能力方面,买方或许比卖方拥有相对更大的市场势力;因此,这些行业的买方可以运用市场势力更有效地约束卖方,而不是卖方约束买方。某些行业的卖方也可能更依赖买方,而不是相反。根据边际买方的需求弹性和总供给量,市场份额相对较低的企业可以享受与市场份额较高的企业一样多(甚至更多)的买方势力。(**可以说,市场份额阈值对于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的诉讼请求都是武断的。事实上,尽管市场份额相对较低,但显示买方垄断势力的因素同样可能显示卖方垄断势力。换言之,当边际卖方的供给弹性和消费者需求弹性都很低时,(譬如)拥有43%市场份额的企业也可以运用其垄断势力。然而,原告很少质疑反垄断判例法的市场份额阈值本身。相反,诉讼人通常会争论应该更宽泛还是更狭窄地界定市场。)
然而,误报的问题依然存在。买方垄断者的市场份额可能很低,但许多市场份额低的买家并不是买方垄断者。同样,从拥有较高市场份额的角度看,所有买方垄断者都具有买方势力,但并非所有具有买方势力的企业都是买方垄断者。(***参见Health Report at ch 6,*18(引自注释57)(指出“由于管理式医疗的目的之一是将价格降低至接近竞争水平,因此很难确定管理式医疗的买方何时行使其买方垄断势力”)。)卖方产量减少绝不是买方垄断的标志;譬如,买方可以实施价格歧视。
因此,在评估上游滥用市场势力的行为时,反垄断机构和法院应根据情况做出相关调整。被指控的买方垄断者的市场份额越低,原告在以下方面的举证责任就越大:(1)边际买方无法获得卖方更多的产出;(2)卖方无法在其他地区或向其他买方轻松、廉价地生产和销售其他产品。当然,这有时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被告可以是“市场上精明的行动者”(****Southeastern Milk,801 F Supp 2d at 727),而未必是买方垄断者。
如此一来,经验法则就是买方是否有胁迫行为。(*关于根据外国法律考虑强制标准的问题,见Albert AFoer,Abuse of Superior Bargaining Position(ASBP):What Can We Learn from Our Trading Partners?(American Antitrust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16-02,Sept 29,2016),存档于https://permacc/37U7-DNHW。)胁迫隐含了边际买方的需求弹性和总供给量;由于卖方的价格被压低,几乎没有其他买方或替代销售机会可以救助被剥削的卖方,使其摆脱买方的束缚。尽管市场势力“通常由卖方占有的主要市场份额推断得出”,(**Eastman Kodak Co诉Image Technical Services,Inc,504 US 451,464(1992)。)但最高法院解释说,潜在的市场势力具有强制性,即“强迫买方做他在竞争市场中不会做的事情”。(***同上,引用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District No 2诉Hyde,466 US 2,14(1984)。)有越多的证据表明企业胁迫卖方做他们在竞争市场中不会做的事情,企业就越有可能拥有买方势力,即使它的市场份额相对较低。买方胁迫的证据越充分,对买方垄断势力的推断就越有力。
此外,有确凿证据显示,主要的买方垄断者可以向上游投射2—3倍的买方垄断势力。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强大的零售业和制造业经销商可以从供应商那里获得实质性的价格优惠,反过来,供应商会降低其员工的工资,提供更差的工作条件。(****参见Nathan Wilmers,Wage Stagnation and Buyer Power:How Buyer-Supplier Relations Affect U.S.Workers- Wages,1978 to 2014,83 Am Sociological Rev,第213页、第215—216页(2018)。)
关注上游是至关重要的,毕竟最近的经济证据表明,劳动力市场集中对工资产生了向下的压力,促使雇主将培训成本转嫁给工人,并导致在劳动力市场招聘员工的企业之间出现更大的不平等。(*****参见Jose Azar,Ioana Marinescu,and Marshall ISteinbaum,Labor Market Concentration(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4147,Feb 2017),存档于https://permacc/Y5CUKSN5。另见Baker,Antitrust Paradigm,第22页(引自注释22)。也可参见Brad Hershbein and Claudia Macaluso,Labor 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Skills(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Working Paper,July 2018),存档于https://permacc/TYY5S8BG;David Berger,Kyle Herkenhoff,and Simon Mongey,Labor Market Power(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No 12276,Apr 2019),存档于https://permacc/NWA8-4LZH。)为了使反垄断机构习惯于关注上游,有效竞争标准将要求这些机构和法院考虑合并是否可能大幅削弱竞争,或趋于对上游劳动力、供应商和产品市场形成买方垄断。(******有关早期方法的缺陷以及上游限制和合并造成的损害,参见Carstensen,Competition Policy,第105—116页、第128—131页、第260—163页(引自注释36);Krueger and Posner,Policy Proposal,第12页(引自注释47)(建议在各机构的合并指南中增加新的章节,指导政府根据合并对劳动力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筛查合并)。)《谢尔曼法案》下的改革也将适用于上游,包括买方垄断的诉讼请求和反竞争限制。效率诉由不能用于为被告在上游市场的反竞争行为辩护。
3.6超越价格影响的框架
反垄断机构认识到,反竞争行为不仅会影响价格和产出,还会影响隐私保护、质量、品种、服务和创新。尽管如此,法院通常以“相关市场的产出减少和价格上涨”衡量竞争受到的损害。(*Sterling Merchandising,Inc诉Nestle,SA,656 F3d 112,121(1stCir 2011)(重点省略)。)正如乔纳森·贝克教授(Jon Baker)所说:
如果竞争在价格以外的其他维度受到损害,例如质量或创新,那么价格(或质量调整后的价格)是否超过竞争水平也将无关紧要。反垄断的问题在于,竞争减弱是否使贸易条件相对于竞争没有减弱时更不利于买方,而不论企业竞争的维度或价格的绝对水平如何。(**Baker,Antitrust Paradigm,第180页(引自注释22)。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有效竞争标准将要求法院和反垄断机构在合并、反竞争行为、卖方垄断和买方垄断案件中不仅仅关注价格受到的影响,还要关注其他重要的非价格竞争参数(如质量、选择、隐私等)受到的影响。在权衡这些影响时,法院不应像通常那样,在没有赔偿机制的情况下,用一组利益相关者获得的利益抵消另一组利益相关者受到的竞争损害。
有效竞争标准还将承认,企业在违反反垄断法的同时,还违反了旨在保护被排除在经济之外或被边缘化的既有弱势群体的其他法律(如民权法),其损害可能会加剧。这应该包括根据既有弱势群体的种族和身份进行的非法的市场配置。
3.7补救措施
有效竞争标准将优先采取结构性补救措施。讽刺的是,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诉美国一案(***221 US 1(1911))引入的合理原则分析最终变得拙劣不堪,而最高法院也支持强有力的结构性救济措施,包括打破卖方垄断和买方垄断格局。(****同上,第77—82页。)
因此,执法者至少需要防止卖方垄断或买方垄断愈演愈烈。这意味着执行《克莱顿法案》和《谢尔曼法案》的宗旨:打击集中化趋势和反竞争行为,譬如谷歌把搜索引擎流量转移到自己的比对购物服务上,同时把竞争对手的服务放在搜索结果中不太显眼的位置。(*参见European Commission,39740 Google Search(Shopping)*103-08(2017),存档于https://permacc/CJU6-W7VA。)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些反竞争风险出现之初就遏止它们。
这也意味着阻止合并,而不是允许在各种行为条件下合并(如康卡斯特合并NBCU(**参见Modified Final Judgment,United States诉Comcast Corp,No 1:11-cv-00106,*9-14(DDC filed Aug 21,2013)。)、谷歌合并ITA软件(***参见Final Judgment,United States诉Google Inc,No 1:11-cv-00688,*13-27(DDCfiled Oct 5,2011)。)和Ticketmaster合并Live Nation(****参见Final Judgment,United States诉Ticketmaster Entertainment,Inc,No 1:10-cv-00139,*8-14(DDC filed July 30,2010)。))。
4.如何将有效竞争标准落实到联邦反垄断政策中?
现行的消费者福利标准并不是法定的。它代表了芝加哥学派、后芝加哥学派和哈佛学派拥护者提倡的有利于整合和纵向一体化的产业政策。鉴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消费者福利标准无法保护竞争和消费者,并且存在操作困难,这一标准应予以废除。
这样,我们不妨通过五个不同的途径纠正市场势力问题:
第一,在没有任何立法行动的情况下,法院和反垄断机构可以按照国会的意图执行联邦反垄断法。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这样做。有效竞争标准虽然是新的,但与《谢尔曼法案》和《克莱顿法案》的立法目的是一致的。
第二,联邦贸易委员会可以按照国会的意图,行使《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赋予的权力,(*****38 Stat 717(1914),根据《美国法典》第15编第41节做出修订。)通过制定规则来处理这些反竞争行为和合并。(******关于联邦贸易委员会制定规则的辩护,也可参见Comment of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er Rohit Chopra,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21st Century,Hearing Before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2018),存档于https://permacc/Q4E9-U6LQ。)
第三,国会可以修订《谢尔曼法案》和《克莱顿法案》,以明确规定有效竞争标准,并对常见的反竞争限制进行法律推定以实施这一标准。
第四,国会可以颁布新的民事反垄断法规,也可以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根据新标准对具体的本身违法原则和推定制定法规。
最后,国会可以选择不通过有效竞争的法律标准本身,而是通过其他具体措施实施这一标准(如前面第3节所述)。
前两个选项是可行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旨在将该机构的职权扩大到《克莱顿法案》和《谢尔曼法案》之外。但是,联邦司法机构的组成、为弥补最高法院偏离经济理论所致损害而花费的时间和金钱、阻碍反垄断机构改变现状的各种因素,以及在此期间对公众造成的持续伤害,所有这些都需要采取立法行动。鉴于更精英化的政府部门未能保护竞争,民主问责部门的介入是恰合时宜的。
这就引出了第三和第四个选项。在其他司法辖区,例如德国,最近更新了其针对数字经济的竞争法。(*例如2017年,德国修订了竞争法,规定在评估企业市场地位时应考虑直接和间接的网络效应。Act Against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18(3(a))(Competition Act—GWB),2017年10月30日由该法案第10条第9款最后修订,存档于https://permacc/Y8XH-ZTMP。2019年,德国提出了补充修正案以保护数字平台经济中的竞争,包括要求企业在评估市场势力时获取与竞争相关的数据。参见Draft Proposal for the 10th Amendment of the German Competition Act(D Kart,Oct 7,2019),存档于https://permacc/5PA3-5543。)虽然美国国会多年来一直在修订联邦反垄断法,但六十多年来都未曾显著改变反垄断法的实质。(**参见Federal Trade Commission,The Antitrust Laws,存档于https://permacc/3SSF-YY5K。)部分原因可能是《谢尔曼法案》和《克莱顿法案》被视为普通法。另一个原因是《谢尔曼法案》规定了刑事和民事责任。(***15 USC§§2,15(a)-(h))毫无疑问,任何法律上的改变都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在修订美国竞争法时,国会可能面临一个问题:是否只需要更改标准(例如添加有效竞争标准的内容)和(或)具体的推定以及本身违法原则,就可以推广有效竞争标准。
在法治原则下,司法机构的作用应该是根据原法律以及遵循原法律的先例解释反垄断法。它不应根据其认为的有关竞争政策的最新经济思想解释行为。(*参见Spencer Weber Waller,Microsoft and Trinko:A Tale of Two Courts,2006 Utah L Rev 741,749(“在Trinko一案中,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表态只是赤裸裸地主张一种政策偏好,而自反垄断法通过后,这种政策偏好就不被接纳”)。)通过宣布具体的原则,国会将确保法院能在法治的前提下解释反垄断法以推进这些原则,同时限制法院任意达成违背这些原则的标准(或裁决)。
因此,我们主张纳入两个部分:第一,国会应该认识到,反垄断法不是单一地定义竞争损害,而始终是促进多重经济、政治和社会目标。每个国家的竞争法都可能包含多个目标,却不一定对目标排序。
问题不在于竞争政策是否应该纳入非经济价值观,而在于法院和执法者在分析、权衡多个目标和多个利益相关者时,应该拥有多大的自由度。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法院目前用于评估大多数反垄断诉讼请求的合理原则存在缺陷。通常,我们不可能既有符合法治的事实专用型衡量标准(factspecific weighing standard),比如合理原则,又能实现多重目标。任由反垄断机构和法院在每一起反垄断案件中都掺杂各种目标,只会带来灾难。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法院能否在空洞的合理原则中系统地实现多个目标,是值得怀疑的,无论它们是应用消费者福利标准还是有效竞争标准。此外,允许它们掺杂各种目标,会给错误和政治俘获制造更多的机会。
因此,除了提出承认反垄断有多重目标的有效竞争标准外,我们倡导的第二个重要部分是,从最高法院笨拙的合理原则转向更明确的法律推定。国会可以促使最高法院从关注“案件记录中披露的特定事实”这种个案式合理原则分析,(**Eastman Kodak,504 US at 467,引用Maple Flooring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诉United States,268 US 563,579(1925)。)转向更简单的反垄断推定和“清晰到律师足以向客户解释”的规则。(***Pacific Bell Telephone Co v linkLine Communications,Inc,555 US 438,453(2009),引用Concord v Boston Edison Co,915 F2d 17,22(1st Cir 1990)。)只要可行,我们建议的这一立法将从直接规范市场参与者的事后行为,转变为运用法律推定,寻求事前促进竞争结构并维护其中的自由。
这将使反垄断执法大大简化而不是复杂化。(*当前的合理原则审查“是数据密集型的,因此对诉讼人而言成本高昂;此外,它会消耗大量的法庭时间和其他资源”。California诉Safeway,Inc,651 F3d 1118,1146(9th Cir 2011)(Reinhardt法官部分赞同,部分反对)。)难怪鲜有反垄断原告能够负担得起此类诉讼。
在理想情况下,国会应制定有效竞争标准,同时制定简单到律师可以向客户解释、反垄断机构可以执行、法院可以适用的法律推定。
此外,有效的竞争标准将扩展反垄断原告可使用的损害理论,进而使被告利用经济理论对消费者提价或减产的策略失去效力。因此,虽然反垄断执法的政策目标的确会随着有效竞争标准而扩张(相对于根据消费者福利标准提出的目标),但是我们建议的标准与法律推定相结合,将显著减轻单个执法行为的行政负担,最终使反垄断回归执法本位,而非高度程式化的理论推测。
结论
今天,美国经济和社会存在以下不协调现象:
第一,当前的反垄断政策宣称要促进消费者福利,但这并没有发生。(**Steinbaum and Stucke,Effective Competition at 22-28(引自注释20)。)
第二,法院经常宣告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而不是单个竞争者。(***例如参见Starlight Cinemas诉Regal Entertainment Group,691 F Appx 404,405(9th Cir 2017),引用AT&T Mobility LLC诉AU Optronics Corp,707 F3d 1106,1112(9th Cir 2013)。这一说法来源于Brown Shoe,370 US,第344页(“《法案》保护的是竞争,而不是竞争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的法院通常在做出这一陈述后立即无视最高法院的声明:
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国会希望通过保护有生存能力的地方小企业来促进竞争。国会意识到,维护分散的行业和市场可能会导致成本和价格偶尔上涨。它解决了这些竞争因素,以利于分散权力。我们必须执行这一裁决。
现在的法院也无视最高法院在Brown Shoe案中对1950年《克莱顿法案》修正案中的国会意图所做的深入探讨:“国会审议1950年修正案的首要主题,是担心美国经济集中度日益上升的趋势。”同上,第315页。1950年立法的“其他支持因素”是“希望保留对行业的‘地方控制’和保护小企业。”同上,第315—316页。最近的一个例子,参见大法官Neil Gorsuch早期对美国运通公司口头辩论的干预。Transcript of Oral Argument,Ohio诉 American Express Co,No 16-1454,*4(US filed Feb 26,2018)(可查阅Westlaw at 2018 WL 1050562)(“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保护竞争者……甚至也不是为了保护商人”)。)可是由于法院和反垄断机构的基本不干预政策,竞争已经减弱。
第三,尽管最高法院最近一直抱怨反垄断诉讼的现状(无休止的诉讼、不可避免的高昂成本和拖拉的调查取证,以及下级法院裁决结果不一致的高风险),然而,制造这种困境的正是最高法院本身。(*参见Maurice EStucke,Does the Rule of Reason Violate the Rule of Law?,42 UC Davis L Rev 1375,1378(2009)。)在过去40年中,最高法院越来越依赖其事实专用型衡量标准(合理原则)和模糊的经济目标(消费者福利),而这两者都包含不同的个人价值观和解释,而且往往没有具体的行动方针。
第四,虽然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动态竞争更重要,但反垄断机构和法院往往规避动态效率分析,而关注静态价格竞争和生产效率。(**参见Brodley,62 NYU L Rev at 1026(引自注释5)。)并且,就反垄断将经济剩余分配给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立场而言,对价格影响的狭隘关注,也为以其他方式损害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的商业模式开辟了巨大空间,譬如收集数据出售给第三方、在质量上区别对待、分割市场,以及阻碍消费者获得有创新精神的进入者和可替代的供应来源。(***另见Marshall Steinbaum、Eric Harris Bernstein and John Sturm,Powerless:How Lax Antitrust and Concentrated Market Power Rig the Economy Against American Workers、Consumers and Communities(Roosevelt Institute,2018年2月),存档于https://permacc/8S9V-RVVA。)
第五是经济权力悖论。美国的宪法框架寻求分散权力,而不是促进权力集中。尽管历史上人们一直关注经济权力的集中,但在威瑞森通信公司诉柯蒂斯·多林克律师事务所(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 诉Law Offices of Curtis V.Trinko)一案中,(****540 US 398(2004))最高法院支持垄断价格是自由市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上,见第407页(“单纯拥有垄断势力,同时收取垄断价格,不仅不违法,它还是自由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回归《谢尔曼法案》的国会宗旨后,最高法院最近更多是在谴责而不是赞成垄断定价。Apple Inc诉Pepper,139 S Ct 1514,1525(2019)(“自1890年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并由本杰明·哈里森总统签署《谢尔曼法案》以来,保护消费者免受垄断价格侵扰一直是反垄断的核心问题”)。尽管如此,多林克律师事务所的辩词在下级法院和反垄断机构中仍然产生了新的含义。例如参见United States' Statement of Interest Concerning Qualcomm's Motion for Partial Stay of Injunction Pending Appeal,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诉Qualcomm Inc,No 5:17-cv-00220-LHK,*4(9th Cir filed July 16,2019)(可查阅Westlaw,2019 WL 3306496)(司法部主张支持垄断,反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行动和下级法院的裁决,认为“收取高价并非反竞争”)。)
面对买方垄断势力、止赎权、强大的经销商支配市场,以及反垄断法试图纠正的许多其他滥用行为,对消费者福利标准的解释和执行不仅背离了其本意,还带来了损害,这表明,我们必须推行实质性的改革。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当前的反垄断政策失败重重,促进竞争已是当务之急。为此,制定新的标准和新的法律推定以促进有效竞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不可避免。■
(颜超凡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