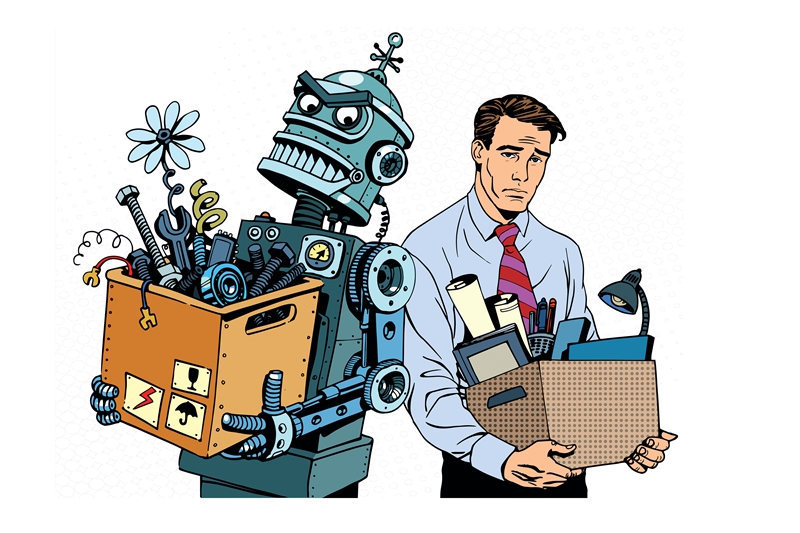*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Pascual Restrepo,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作者衷心感谢Chris Ackerman、David Autor、Erik Brynjolfsson、Stu Feldman、Mike Piore、Jim Poterba和Hal Varian对本文的宝贵评论。此外,我们真诚地感谢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斯隆基金会(Sloan Foundation)、图卢兹信息技术网络(Toulouse Network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施密特科学基金会(Schmidt Sciences Foundation)、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Smith Richardson Foundation)、IBM、埃森哲(Accenture)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为本研究提供的财务支持。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观点。
您正在阅读
阿西莫格鲁:错误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与未来的劳动力需求
有效期:-
您可在 个人中心 - 我的权限 - 单篇 找到购买的文章
您正在阅读
阿西莫格鲁:错误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与未来的劳动力需求
¥0 购买单篇 继续阅读
限时优惠,共可读 1 篇相关稿件
我已订阅,切换账号登录
[《比较》印刷版,点此订阅,随时起刊,免费快递。]
版面编辑:吴秋晗
相关阅读
- 2019年03月01日
- 2018年06月21日
- 2018年06月21日
- 2018年06月21日
财新网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财新传媒及/或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如有意愿转载,请发邮件至hello@caixin.com,获得书面确认及授权后,方可转载。
免费订阅财新网主编精选版电邮
财新移动



 页面加载中...
页面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