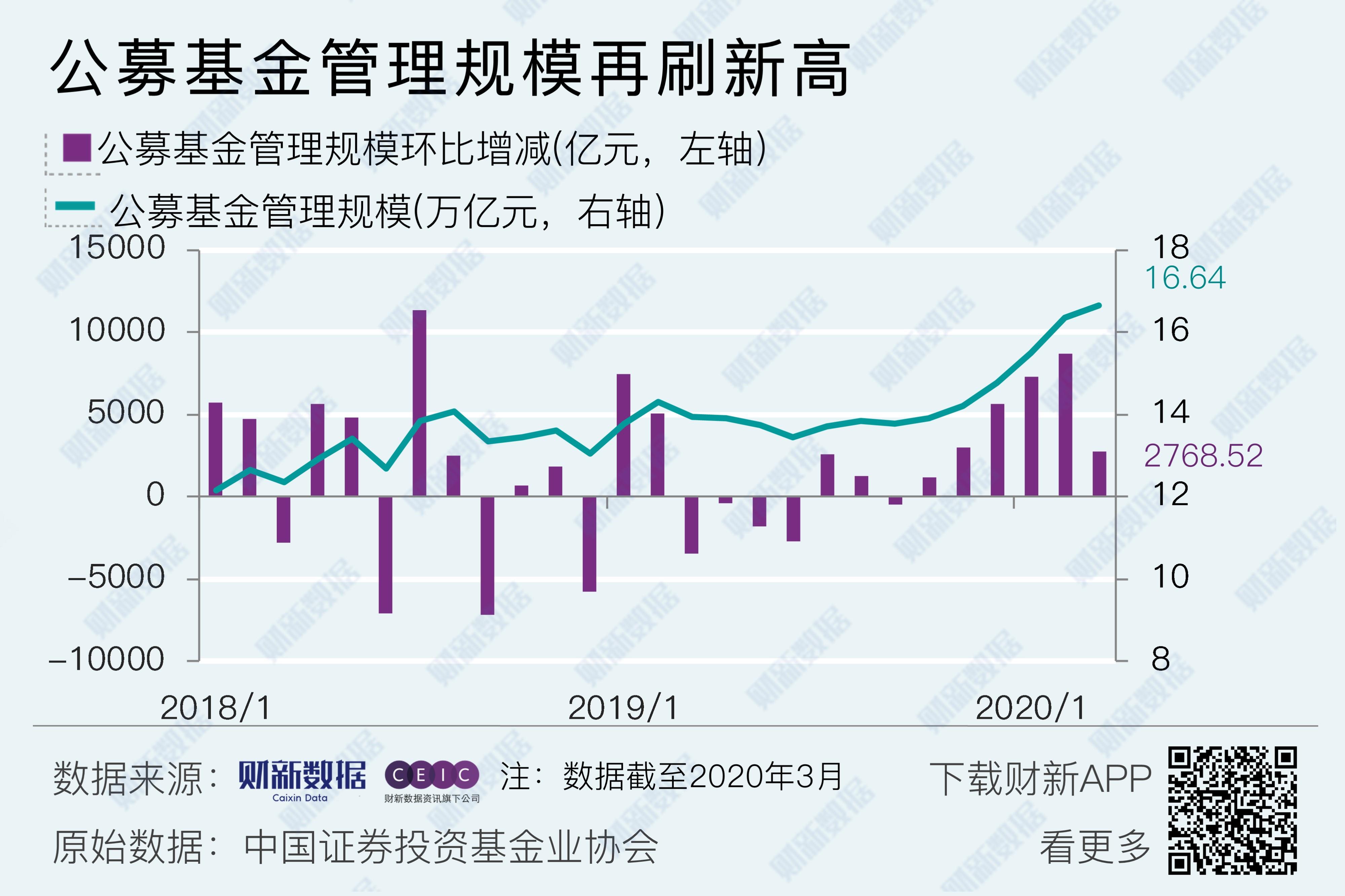*Giulio Federico, 欧盟竞争管理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团队的负责人;Fiona Scott Morton,耶鲁大学管理学院Theodore Nierenberg经济学讲席教授;Carl Shapiro,伯克利加州大学哈斯商学院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被解释为欧盟委员会的正式立场。作者感谢Mike Andrews、Richard Gilbert、Gregor Langus、Angel Lopez和 Scott Stern对本文初稿的评论。有关致谢、研究支持的来源以及作者重要财务关系的信息披露,请参见https://www.nber.org/chapters/c14261.ack。(因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附录部分,特向作译者和读者致歉。有需要者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citicpub.com。——编者注)
1.引言
我们赞美市场颠覆者,那些改变现状、威胁在位企业,有时甚至改变整个行业的企业。熊彼特将这个过程称为“创造性破坏”。通过这个过程,具有破坏性的企业促进了经济增长,并将新技术与新商业实践和商业模式的好处带给消费者。
我们关注的是反垄断政策对创新的影响,反垄断政策也被统称为竞争政策。(*1.竞争政策与促进创新的其他基本公共政策共同发挥作用,包括知识产权政策、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培养技能劳动力的政策以及维持健全金融体系的政策。我们的反垄断分析采用了这些政策。)竞争政策力求保护和促进充满活力的竞争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新创意转化为被实现的消费者利益。从根本上说,竞争促进了创新。关于生产率和增长的文献告诉我们,随着时间推移,创新是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动力,因此通过有效的竞争政策促进创新很可能对经济增长和福利都非常重要。
大量的创新是由颠覆性企业驱动的。(*2.我们广泛地使用“颠覆”一词来表示挑战现状的大量活动。Gans(2016)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颠覆概念。这个概念是从当前市场领导者的角度出发的:“当成功的企业由于持续做出使它们成功的决定而失败之时。”)颠覆性企业不会使用与在位企业相同的技术或商业模式。它们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价值主张,而不仅仅是更低的价格。以一种新的方式向顾客提供有吸引力的产品或服务,颠覆性企业可以在创造大量消费者剩余的同时,大量摧毁在位企业的利润。随着新产品的进入和旧产品的退出,以及新的商业方法和商业模式取代旧的商业方法和商业模式,产品和市场份额的剧烈波动代表了一个健康的竞争过程。如果这种竞争过程因合并或排他行为而减慢或有所偏向,创新就会减少,消费者就会受到损害。同样的竞争过程可促进最佳实践的发展和扩散,其中包括可称为减少X无效率(X-inefficiency)的那些实践。贸易和生产率方面的文献都令人信服地表明,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差异显著,更激烈的竞争会将销售量重新分配给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如果销售量是可竞争的,就可促进最佳实践的扩散,传播到业绩更好的企业。竞争政策旨在保护竞争过程,通过这一过程,颠覆性企业可以挑战现状。竞争政策不关注其涉及的企业类型或创新类型。快速成长的初创企业肯定会造成破坏,优步和爱彼迎就是两个近来的突出例子。但是,大型老牌企业也可能造成破坏,尤其是当它们进攻邻近市场时。试想沃尔玛进入当地零售市场,微软的必应在搜索领域挑战谷歌,或者网飞(Netflix)制作自己的视频内容。
相比之下,在位的成功企业在其核心市场中扮演的角色却存在严重的冲突。一方面,降低成本的流程创新对最大的企业最有价值,而且市场领导者经常投入大量资金引进新一代产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英特尔开发新一代技术,并建立新的晶圆厂生产微处理器;波音公司开发新一代大型商用飞机;威瑞森(Verizon)投资建设5G无线网络。事实上,正如熊彼特在75年前观察到的,在经历快速技术变革的许多行业中,最大的企业也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新者。考虑到研发的规模经济,尤其是在开发下一代产品或流程需要数亿美元投资和/或需要对当前技术拥有丰富经验的行业,这应该不足为奇。(*3.最大的企业往往是最成功的创新者,恰恰是因为创新使它们在市场上获得了强大的地位,所以企业规模和创新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一家在位的成功企业如果能从现状中获得巨额利润,就会有很强的激励维持这些利润,这就意味着要减缓或阻止破坏性的威胁。在位的成功企业也会发现投资颠覆性技术在组织上是非常困难的。(*4.这在组织行为学和经济学中是一个古老而有力的观点。例如参见Christensen(1997)和Bresnahan et al.(2012)。)竞争极大地增加了开发新技术的方法的多样性。
我们在本文中强调,当市场领导者可以利用其竞争优势,同时面临来自传统竞争对手和颠覆性市场进入者的压力时,创新能得到最好的促进。企业究竟是市场领导者还是颠覆性市场进入者,则取决于环境:同一家企业可能在一个领域是市场领导者,在另一个领域是颠覆性的新贵。市场领导者可能面临来自同一市场的其他大企业、邻近行业的其他大企业或者颠覆性小企业的竞争压力。识别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不同的情况下,所有这些竞争的来源都是重要的。从历史上看,它们都受到过竞争政策的保护。
我们要分析的中心主题是,如果一个市场领导者担心自己的领导地位会被颠覆性的竞争对手夺走,它就最有动力创新。(*5.Shapiro(2012,第364页)用“可竞争性”原则抓住了这一核心思想:“通过为客户提供更大的价值获得或保护有利可图的销售前景会刺激创新。”)如果明天的大部分销售量将被最具创新力的在位企业或者具有颠覆性的挑战者赢得,如果其他企业能够超越在位企业,那么即使支配型在位企业也会感到创新的压力。一旦人们正确理解了竞争过程的动态本质,就会发现更大的竞争,也即未来在销售量上的更大竞争会带来更多的创新。(*6.下面,我们将讨论并驳斥“更多的竞争可能导致更少的创新”这一相反的命题。这一概念以竞争与创新之间所谓的“倒U形”关系为名,在一些地方扎下了根,并在反垄断中遭到了滥用。)因此,竞争政策的关键作用是防止当前的市场领导者利用其市场势力,要么通过收购潜在的竞争对手,要么通过使用反竞争策略将竞争对手排除在市场之外,消除破坏性威胁。
第2节和第3节讨论了对可能损害创新的横向合并的处理。第4节讨论了对支配型在位企业的商业行为实施的反垄断限制。
2.横向合并与创新:关键的经济概念
本节讨论在横向合并的反垄断分析中使用的关键经济概念,因为人们担心合并可能会对创新的速度和方向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将所有对实际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的合并都纳入“横向合并”的范畴。这里包括了虽然目前没有相互竞争,但基于当前研发或整体能力在未来可能提供竞争产品或服务的企业之间的合并。
我们在这里的分析基于先前有关合并和创新的文献,并更新了这些文献。尤其参见卡茨等人的研究(Katz and Shelanski,2005;Gilbert,2006;Baker,2007;Shapiro,2012)。(*7.关于近期的评论,可参见Baker(2019,第 8章)。)
我们使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和欧盟)反垄断执法机构普遍采用的标准来评估合并:如果合并可能大幅减少竞争,则被视为反竞争。根据这一法律标准,如果合并可能由于竞争减弱而对消费者造成实质性损害,那么合并就是非法的。因此,我们的分析关注合并及合并对双方消费者的影响。这是美国横向合并指南采用的方法。该指南的第六章第四节“创新和产品多样性”描述了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如何评估可能削弱创新的横向合并。欧盟委员会的横向合并指南也关注合并会如何影响消费者。
2.1竞争过程和“业务窃取”
在市场经济中,竞争的最好描述是企业之间的动态竞争过程,其中企业通过提供更好的交易来吸引消费者。竞争促使企业提供更低的价格,并推出新产品和改进后的产品,因为这些活动使成功的企业能够从竞争对手那里赢得有利可图的业务,并保护和维持利润丰厚的现有销售量。(*8.关于作为动态较量(rivalry)过程的竞争原理的历史基础,以及这些历史基础对合并控制的影响,参见Federico(2017)及其中的参考文献。)
这种直接竞争对手之间的动态竞争过程集中在通常所说的“业务窃取效应”(business\|stealing effects)上。业务窃取效应无处不在,因为一家公司通过提供更好的价值赢得消费者,通常是以牺牲竞争对手的利益为代价。业务窃取效应对消费者非常有益,因为它们与企业采取的竞争行为密切相关,而且企业采取竞争行为恰恰是为了使其向市场提供的产品对消费者更有吸引力,从而把消费者从竞争对手那里吸引过来。
我们在这里的重点是创新,所以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当企业从事有风险的投资以开发新产品和改良后的产品,或者开发新生产流程时产生的业务窃取效应。简单地说,我们关注产品创新,但总的来说,我们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流程创新。
虽然某些创新的驱动力来自服务于全新用途的前景,或者来自在价格/成本利润率很低的高度竞争行业中获得销售量的前景,但是创新的许多回报通常是由吸引消费者的前景驱动的,这些消费者原本会购买价格/成本利润率很高的其他产品。例如,当企业竞相在新产品的类别上抢占市场先机,或通过不断的产品改进超越彼此时,这种情况就会出现。
假设A公司已经开发和推出了产品A,但是现在B公司正在投资开发会跟产品A竞争的新产品B。在此情况下,B公司的创新努力对A公司产生了负货币外部性。如果两种产品非常接近于替代品关系,那么产品B对产品A的业务窃取效应最大。重要的是,B公司引入产品B对A公司产生的负货币外部性越大,A公司在产品A上既有的价格/成本利润率就越高。
业务窃取效应对创新激励的重要性早已为人所知。阿罗著名的替代效应(Arrow,1962;Tirole,1988)与创新导致的业务窃取效应密切相关。阿罗分析了同质品市场上的流程创新,在他的模型中,相比于身处创新出现之前的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企业,安全的产品市场垄断企业面临的净创新激励更弱,因为垄断者已经从创新出现之前的现状中获得了大量利润,但是竞争性企业并没有获得类似的利润。(*9.在合并控制政策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认为,阿罗模型刻画了同质品市场中企业合并形成的垄断对创新的影响。这种合并将创新前的利润提高到了垄断水平,从而减少了创新的净收益。然而,阿罗模型并不适合研究实际并购,因为它做出了两个在现实中通常不成立的假设:(1)可能的创新者只有一个,(2)产品市场的竞争耗散了创新前的所有租金。)业务窃取效应也存在于不确定性下的专利竞赛(patent race)模型中。(*10.比如参见Reinganum(1989)。)在这些模型中,相互较量的创新者之间的竞争通常会加速创新,因为任何一家企业都不会将它对其他企业造成的业务窃取效应内部化。(*11.参见Tirole(1988)。)业务窃取效应在内生增长的文献中也得到了明确的认可。比如参见Aghion and Howitt(1992)通过纵向产品差异化建立的“创造性破坏”模型。从这类文献中得到的一个有力结论便是,来自创新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是创新的强大动力。一家安全的在位企业比一家受威胁的在位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要少,因为它不用担心自己的业务会被竞争对手抢走。同样,在关于研发型合资公司的文献中,如果缺乏溢出效应,竞争对手之间的合作会导致创新努力的降低,因为合作将使创新的业务窃取效应内部化。(*12.比如参见d’Aspremont and Jacquemin(1988)以及Lopez and Vives(即将发表)。)
新产品研发竞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为了开发这些产品,企业必须进行有风险的投资。只有当企业认为其产品有足够的利润空间,能够提供足够高的经风险调整后的投资回报率时,它们才会做出这类投资决策。整个创新事业的固有特点就是,成功的产品将获得可观的经营利润,而这又需要价格足够高于边际成本。这样的价格/成本利润率使得业务窃取既能吸引挑战者,又能对在位企业构成威胁。的确,如果产品开发的固定成本很高,而且如果新产品开发有风险,那么在均衡状态下,这些利润率必须相当大,才能证明必要的开发费用是合理的。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合并分析中讨论对创新效应的处理时,重要的是牢记我们讨论的不是价格竞争把价格压低到边际成本的传统行业。这其中的一个关键点是,鼓励创新的行业环境正是通过允许成功的创新者赚取巨大的价格/成本利润,从而使得业务窃取效应更加重要。
2.2对创新的有害影响:业务窃取效应的内部化
在这种动态和创新的市场环境中,人们应该如何评价合并?更具体地说,鉴于拟议的横向合并对合并后的企业通过投资于新产品开发来展开竞争的激励和能力可能产生影响,当评估这些影响时,通常有哪些基本的经济学理论?
为此,首先简要回顾一下如何评估拟议的横向合并对合并后的企业开展价格竞争的激励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会提供一些帮助。一个常见的担心是,两个主要的直接竞争对手之间的合并将消除它们之间的直接竞争,从而导致更高的价格。这一分析将所有其他(非合并)企业带来的竞争视为既定的。这种不利的竞争效应被称为单边价格效应,表明它们是由合并后的实体单方面采取利润最大化行为造成的。单边价格效应可以简单概括为当竞争产品被置于共同所有权之下时,改变价格激励产生的影响。单边价格效应既适用于现有产品,也适用于未来产品。单边效应不同于协调效应(coordinated effects),后者是指合并后的实体和其竞争对手之间的合并后协调(post merger coordination)。
单边价格效应背后关键的经济思想是,合并会将合并双方与定价相关的业务窃取效应内部化,从而导致更少的价格竞争和更高的价格。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这本身就倾向于损害消费者。为了理解基本的逻辑,考虑A公司和B公司的合并。假设A公司销售产品A1和A2,B公司销售产品B,它们都是彼此的不完全替代品,例如早餐麦片或啤酒品牌,又或者不同的汽车型号。在合并之前,A公司在评估产品A1的可能降价时,将基于此次降价对产品A1本身和产品A2的利润会有何影响。在合并之后,合并后的企业在评估产品A1的降价时,将包括此次降价对产品B的影响。对合并后的企业来说,降低产品A1的价格来诱导消费者将消费从B转到A1的吸引力就会降低。由于这个原因,如果合并不能产生协同效应,产品之间存在明显竞争的企业如果合并,就必定会减少价格竞争和损害消费者利益。
我们可以根据合并A公司和B公司使产品之间的业务窃取效应内部化引起的价格上涨压力直接衡量单边价格效应的大小。(*13.参见O’Brien and Salop(2001),Farrell and Shapiro(2010)。)如果这些效应很大,就可以推定合并将导致更高的价格,除非产生了足以抵消这些效应的合并专有(merger\|specific)的成本下降。(*14.参见Werden(1996),Farrell and Shapiro(2010)。)反垄断法通过结构性推定反映了这些基本的经济思想,在结构性推定的框架下,显著提高市场集中度的合并被推定为显著损害竞争。(*15.参见Hovenkamp and Shapiro(2018)。经济分析表明,单边价格效应主要取决于价格/成本利润和被合并企业所售产品之间的交叉需求弹性,但判例法考查市场集中度的做法已经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协同价格效应而不是单边价格效应的历史关注。)人们可以用合并不太可能增强市场势力的证据(例如合并很可能产生原本不能实现的充分的协同效应)反驳该推定。
单边创新效应与单边价格效应非常类似,它关注的是企业投资于新产品开发的决策,而不是其定价决策。评估可能的单边创新效应的第一步,就是寻找合并企业双方与创新相关的业务窃取效应。如果这些效应是显著的,下一步就是寻找可能抵消这些效应的合并特有的协同效应。
举一个在实践中很重要而且特别简单的例子,假设A公司销售一种畅销药,而B公司正在开发一种与之竞争的新药。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A公司和B公司合并会导致合并后的新公司减缓或者完全停止这种新药的研发。(*16.联邦贸易委员会长期关注制药企业的合并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起诉了几起合并。Shapiro(2012)强调Genzyme和Novazyme的合并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表明联邦贸易委员会无法起诉被预测会损害创新的合并。2011年,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一桩合并涉嫌垄断,但最终未能在法庭上胜诉。FTC诉Lundbeck,650 F.3d 1236 (Eight Circuit,2011)。)如果A公司在其畅销药上赚取了很大的利润,并且B公司新药的大部分销售会以A公司的利润为代价(如果根据通常的情况,假设新药和畅销药是同一等级的),那么上述问题就会非常严重。有学者(Cunningham et al.,2019)发现,制药企业的收购具有以下特征:收购那些威胁其当前产品的在研发药物,然后停止其研发。
这里的核心教训是,就像单边价格效应一样,在相关产品的利润率很高而且两家企业之间的业务窃取效应很大的情况下,反竞争的单边创新效应最大。
衡量A公司与B公司合并对B公司创新激励的单边创新效应有一个最简单和最直接的方法,即计算创新扩散率。这个比率被定义为A公司由于B公司成功开发产品B而遭受的预期利润损失,与B公司从成功研发中获得的预期额外利润的比例。(*17.参见Farrell and Shapiro(2010)。)创新扩散率包括了B公司的新产品对A公司所有产品产生的数量效应和价格效应。创新扩散率越高,业务窃取效应就越重要,而合并形成的新公司就越可能按比例缩减或者终止产品B的研发。创新扩散率衡量的是,由于业务窃取效应的内部化,合并后的新公司因为研发产品B而实际上面临的“税”有多高。
在实践中,如果A公司也在进行有风险的产品研发,那么创新扩散率将取决于A公司获得研发成果的可能性以及有条件地取决于B公司的成功。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合并导致的业务窃取效应内部化的程度越高,两家公司研发项目的相关性就越高。在高度的相关性下,合并后的新公司可能会把取消一个研发项目当作消除“重复”项目,但从竞争的角度看,这也消除了两种最终产品相互竞争的可能性。可以预见的是,竞争的这种可能损失会损害消费者。
2.3对创新的有益影响:创新协同效应
合并还可以通过允许两家合并企业之间的有益协调来促进创新。事实上,当两家企业打算合并时,如果存在与创新相关的上述反垄断问题,合并双方通常会主张合并将产生研发协同效应,从而加速创新。这些主张认为,如果没有合并,那么实现可能的协同效应便是不可信的。并且,合并双方对其主张的协同效应要承担举证责任。(*18.美国《横向合并指南》第10节“效率”规定,“拟合并企业必须证明其效率主张,以便司法当局可以通过合理的手段来查证每一种效率实现的可能性和大小、如何以及何时实现(以及实现的成本)、每一种效率将如何提高合并后的企业的能力和竞争激励,以及为何每一种效率都是合并专有的。”)
一种经得起经济分析的协同效应是非自愿溢出效应的内部化。关于技术溢出的文献有很多,包括相互竞争的企业之间的非自愿知识溢出。这种类型的溢出发生在某企业的成功创新是非竞争的并且只有部分排他性的情况下(参见Romer,1990)。例如,一家创新企业的竞争对手可以部分地模仿其新产品而不至于侵犯该企业的知识产权。
理论上,正如夏皮罗(2012)的讨论,非自愿溢出效应的内部化可以部分或完全抵消业务窃取效应内部化导致的创新激励减弱。有两位学者(D’aspremont and Jacquemin,1988)提供了一个早期的理论案例,在该案例中,如果这些溢出效应很大,那么合并可以增加研发投资并使消费者受益。洛佩兹和比韦斯(Lopez and Vives,即将发表)在公司受共同所有权的诱导进行合作的背景下,得到了相似的结果。(*19.Lopez和Vives发现,在差异化产品之间的序贯价格竞争(sequential price competition)中(这是他们考虑的与政策最相关的情形),对于低溢出效应,对称合作减少了研发支出,提高了价格;对于适度的溢出效应,对称合作提高了研发支出和价格;对于高溢出效应,对称合作会增加研发支出并降低价格。他们在固定弹性的伯特兰德模型中,使用数值例子说明了这些结果。)
这项研究支持了如下观点:如果溢出效应足够高,由于合并后的独占效应更高,合并可以增加创新,并最终使消费者受益。然而,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独占效应的影响在重要性上可能都是有限的。例如,非自愿溢出效应的内部化如果可以通过合资的研发企业(RJV)来实现,它就不是合并专有的,因此也就不足为信。与完全合并相比,合资企业的反竞争性更弱,因为它可以在当前和未来的产品市场上保持价格竞争。此外,美国《横向合并指南》规定:“可认知的效率是已得到验证的合并带来的效率,而不是来自对产品或服务的反竞争性减少。”这一规定可被解读为排除了如下观点,即合并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它将减少价格竞争,从而使合并后的实体能够从新开发的产品中独占更大比例的价值。(*20.如果由于这个原因,即使垄断会明显危害消费者也优于竞争,那就需要证明免于反垄断是合理的。在美国运通公司的诉讼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参见Katz and Sallet(2018)以及他们两人在全国专业工程师协会(1978)对美国最高法院制定的法律原则的讨论;以及参见Carlton and Winter(2018)关于价格与非价格竞争的讨论。附录A引用正式经济学模型讨论了单边价格效应和创新激励的关系。)
如果合并有助于拟合并企业之间的自愿技术转让,就会产生第二类创新协同效应。如果合并企业宣称有这类协同效应,它们就有责任证明,如果没有合并(例如,事前的研发型合资企业或者事后的许可协议),就不会发生有益的技术转让。(*21.Motta and Tarantino(2018)建立了一个合资研发企业(RJV)的模型,该模型使两家企业无须完全合并就能在研发投资上获得规模经济。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同时进行定价和投资的博弈中,合资研发企业在研发投资和消费者福利方面都优于合并。)这种协同效应的一个常见例子是合并后的规模足以支持特定的流程创新。此时,合并双方就有责任证明,它们在合并前既无法通过对流程创新的共同研发来实现相同的利益,也无法通过让非创新企业授权流程创新来降低生产成本,或者在创新企业已经从非创新企业那里赢得消费者的情况下,无法实现事后的交易收益。在后一种情况下,根据当事双方以共同接受的提成型专利使用费率(running royalty rate)获得可观的事后交易收益,就简单地断言创新企业不会授权给竞争对手是不够的。
如果两家企业的研发团队合并后能够更有效率地开发新产品,就会产生第三类创新协同效应。美国《横向合并指南》规定:“在评估合并对创新的影响时,各相关部门应当考虑合并后的企业更有效率地从事研究或开发的能力。”这类研发协同效应类似于企业合并后的自愿共享知识效应。这两种效应都依赖于(至少部分依赖于)拟合并企业之间的资产互补性,而且这两种效应都能激励企业从事高成本的研发,其效果类似于将非自愿溢出效应内部化后带来的效果。
(*22.有关合并和创新的最新正式模型考虑了研发协同效应对创新激励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Motta and Tarantino(2018)对合并形成的垄断企业会降低研发成本建模。他们的研究结果与上文中讨论的Lopez and Vives(即将发表)的研究结果实质上是相似的。Federico et al.(2018)在包含了随机产品创新伴随着价格竞争的序贯模型中发现了相似的结果。他们模拟了如下情形:相互竞争的创新者之间的合并提高了它们的创新效率[这可被视为一个代理变量,刻画合并产生的自愿知识溢出效应的赋能影响(impact of enablement)]。在他们的模拟中,创新效率的提高存在一个中间水平,在这个水平上,每个拟合并企业的创新努力保持在合并前的水平(刚好抵消了创新扩散的负面影响)。合并后的创新效率提高,抵消了合并对整体消费者福利的负面影响(因此也减轻了合并对现有产品和创新产品价格竞争的不利影响)。)
合并的这种研发协同效应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并双方是如何从事研发的,以及两家企业是否具有互补的能力。这种研发协同效应是企业内部互补资产组合产生的广泛得多的协同效应中的一个特例。理论上,合并后的新企业可以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或者综合互补的研发能力,从而降低研发增量成本。(*23.研发增量成本(incremental R&D cost)是指随着研发工作水平而在边际上变化的成本。研发增量成本的减少意味着,对于任何给定的研发工作水平,研发总成本减少(即研发成本曲线向下平移和/或变平)。)如果合并可以降低研发的增量成本,那它自然就会增强企业从事研发的激励。评估旨在实现这种协同效应的合并往往要对特定事实进行调查。
在实践中,区分合并带来的研发增量成本下降与取消同一领域研发项目带来的成本节约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熟悉的成本曲线偏移或倾斜与沿着成本曲线移动之间的区别。后者并不是对消费者有利的效率。相反,关于在合并后打算取消所谓的“重复性”研发项目的证据直接表明,合并可能导致抑制创新的反竞争。(*24.美国《横向合并指南》明确指出了这一担忧:“研发成本的节省可能是巨大的,但并不是可认知的效率,因为它们难以核实或者产生于反竞争的创新活动减少。”欧盟委员会《横向合并指南》(第80段)也含蓄地指出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重复性”研发项目这个提法可能只是“竞争性”研发项目的一种委婉说法,就像合并公司消除“重复性”产品或零售店一样。合并后,相互较量的创新者之间的创新竞争不复存在,这自然有可能抑制竞争性的研发项目。
在分析研发协同效应的同时,实践中还必须考虑一种现实危险,即合并将导致研发反协同效应(dis\|synergies)。出现研发反协同效应的原因多种多样,在某些情况下,是由于高技能人才离开合并后的企业。出现研发反协同效应的更根本原因是,合并后的企业无法有组织地用多种方法开发新产品或者解决某些业务问题。这种危险在关于商业战略的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分析。这种反协同效应可能很大,合并分析不应忽视它。(*25.Sah and Stiglitz(1987)、Bresnahan et al.(2012)也发现了与组织多样化的价值相关的类似观点。Rubinfeld and Hoven(2001)讨论了对研发多样化展开竞争的好处,并将它们具体应用于美国国防产业的合并执法。关于竞争和研发多样化的正式模型,参见Letina(2016)和Gilbert(2019b)。)换句话说,与单个组织的实际支持相比,多组织之间的竞争可能产生更多样化的方法。
最终,合并双方必须证明,它们主张的任何创新协同效应(1)可能来自合并,(2)用另一种可以保留更多竞争的安排无法实现,以及(3)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大体上既能够抵消合并引起的创新激励减少,还能抵消单边价格效应(不包括生产成本的任何节约)对当前和未来产品市场竞争的危害以及对消费者的损害。
2.4关于“竞争和创新”的误导性经济学文献
尽管与业务窃取效应内部化相关的令人信服的经济学逻辑为分析横向合并的创新效应提供了清晰的程序,但还是出现了一种说法,这一说法基于“竞争和创新”的大量文献,认为反垄断的执法者在创新方面应当宽容横向合并,因为“过多的竞争可能对创新有害”。这一说法被总结为“竞争”和“创新”之间所谓的倒U形关系。(*26.尤其是参见Aghion et al.(2005)以及Aghion and Griffith(2005)。)不出所料,“过多的竞争可能对创新有害”这一说法已经在寻求合并的企业中流行起来。(*27.例如,在欧洲移动电话行业整合的背景下,行业协会使用了这一观点,参见BCG/ETNO,“Reforming Europe's Telecoms Regulation to Enable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2013);Frontier Economics/GSMA,“European Mobile Network Operators Mergers”(2014)。)然而,如果更仔细地阅读文献,就不会得出这一结论。
为了解个中原因,可以假定一个行业,该行业处于零预期利润和自由进入的均衡状态,并且有显著的边际成本加成,此时,市场进入和竞争的动态过程是不受阻碍的。假设创新是该行业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创新将在某种均衡水平上由企业研发投资驱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可能会提出的一类问题是,创新的均衡水平将如何随市场特征变化,比如市场规模或消费者重视多样化的程度。这类问题通常在文献中被提出来,例如,如果模型中的产品差异化更大,创新程度会更高还是更低。然而,这种类型的比较静态问题与合并控制政策没有直接关系,并且这种文献在实践中被误解和误用了。
在本文中,我们关注的是有关竞争政策的经济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假定市场特征不变,包括需求结构、产品特征和公司的成本函数,并力图预测当合并或者排他行为导致竞争减弱时创新会有什么变化。由于前文所述的原因,如果没有协同效应,重要竞争对手之间的合并可能会导致创新减少。“过多的竞争可能会对创新有害”这一误导性说法从根本上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问题:(1)行业的潜在需求或成本条件变化对创新产生的影响,以及(2)当行业的基本情况不变时,两家对手企业计划的合并对创新产生的影响。
夏皮罗(2012)详细论述了“过多的竞争可能对创新有害”这一命题。他强调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更多的竞争——意味着未来的销售竞争更激烈——会刺激创新。他还指出,文献中使用的模型通常不分析合并的影响,而是着眼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的外生变化。(*28.这些文献的模型通常考虑产品市场竞争强度的变化,但没有考虑(合并带来的)研发活动协同的影响。这种方法最多只能部分反映合并对研发激励的影响。这些文献还利用一些代理变量来模拟产品市场竞争的变化,但这些变量没有明确刻画两家对手企业合并的影响的代理参数。例如,这些文献经常关注市场参数的变化,如产品差异化程度、来自竞争边缘的约束强度或行业需求的价格弹性。产品市场竞争强度的这些外生变化并不是刻画合并影响的好的代理变量。这些文献中的一些模型也考察了企业数量和相应产品的外生变化对创新的影响;参见Vives(2008),以及最近的Gilbert et al.(2018)、Marshall and Parra(2018)。这种方法也没有说明合并的影响,因为合并允许两家公司在研发努力和价格方面进行决策协同,而并不意味着其中一家企业的资产和产品会消失。这些文献通常也没有考虑(假设的)某企业/产品消失导致的产品种类减少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寡头环境中的合并和创新正式模型,可参见Igami and Uetake(2019),Motta and Tarantino(2018),而Federico et al.(2018)并不支持倒U形的理论预测。)这些被引用的论文的作者通常不会声称他们的分析适用于合并的反垄断分析。
3.横向合并和创新:应用和案例分析
现在我们讨论这些思想在实践中的应用,包括对美国和欧洲一些重要的具体案例的讨论。我们将分析分为三个部分,反映了在实践中出现的三种不同的事实模式。
第一,我们考虑在开发规划(development pipeline)中有可识别产品或项目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合并。这类情况包括现有产品和规划产品的重叠(product\|to\|pipeline overlap),其中一家企业拥有某种产品,而另一家企业正在开发竞争产品。这类案例通常涉及相对短期的创新竞争。这类情况还包括规划产品之间的重叠(pipeline\|to\|pipeline overlap),其中每家企业都在开发新产品,如果同时推出这两种产品,产品之间会相互竞争。这类案例通常涉及中期的创新竞争。
第二,我们考虑具有创新竞争能力的老牌企业之间的合并。这些案例牵涉长期的创新竞争。这两种案例并不互相排斥;例如,合并很容易涉及可识别的竞争性规划产品以及能力重叠,而能力重叠引发对创新遭受损害的长期担忧。
第三,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情况:一家支配型大企业试图收购一家拥有创新能力的小企业,其创新能力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发展成为一种威胁。尽管未来产品的重叠可能还难以辨别,但是这些案例可能涉及颠覆性的市场进入者。
我们关注的是单边创新效应,但这些效应通常伴随着对未来产品的单边价格效应而生。在实践中,相较于分析对现有产品的单边价格效应,分析对未来产品的单边价格效应可能更具挑战性,原因有二:(1)这些未来产品是否以及何时会被引进,引进后的产品有怎样的属性,通常是不确定的;(2)由于缺乏可用的数据,未来产品的替代模式通常难以衡量。缺乏数据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反垄断问题。
更一般地说,当我们着手于应用并关注案例研究时,需要注意的是,分析拟议中的合并对创新的影响必然是一项涉及大量不确定性的预测工作。事实上,拟合并企业经常争辩说,任何关于合并损害创新的担忧都是猜测性的,因为开发新产品的过程是不确定的,未来的市场状况难以预测,竞争可能产生于意料之外的来源。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们并没有为消除业务窃取效应内部化对创新的损害提供可靠的基础。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持相反的观点:相比于只是将竞争性产品联合起来的合并,将创新对手联合起来的合并更令人担忧,因为创新可以强有力地推动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和经济增长。此外,合并双方声称合并将产生创新协同效应,但这也可能涉及大量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是狂妄自大。
在实践中,回应拟合并企业关于“合并的创新效应都是猜测性的”辩护引发了一个问题,即我们究竟是更多地关注前文提及的一般性经济学原理,还是更多地关注具体的产品或研发项目,而关于这个问题的可用证据数量因案件而异,有时非常有限。在实践中,关于两种尚未上市的产品如何相互竞争,或者它们各自的销售情况如何,几乎没有现实世界的证据。人们最多能做一些预测,而这些预测在产品发布之前几乎都不可用,部分是因为每家企业通常对其他企业的研发情况了解有限,从而使企业很难研究和预测其产品将如何竞争。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未来竞争的具体情况越难辨别,依靠前文提及的一般性经济学原理就越明智。要求政府提供未来竞争的精确定量证据,以满足其关于单边创新效应的举证责任,就等同于放弃与未来产品研发相关的合并执法,而这些产品尚处于研发阶段早期或者尚未被发现。(*29.相关讨论参见Kwoka(2018,第二章)。)
3.1现有产品和规划产品的重叠和规划产品之间的重叠
如果拟合并企业中的一家或两家都拥有一个正在研发或考虑但尚未进入市场的特定项目,就会出现这两种类型的重叠。规划产品的一个主要例子是已经被发现但仍在研发中的某一种药品(或分子)。药品研发可能需要多年时间,并且需要大量投资于有关药品疗效和潜在副作用的科学测试。
在某些部门,特别是制药部门和农用化学品部门,研发规划受监管要求的影响,因此是一个结构有序的过程。这些研发规划可以跨越许多年,并涉及许多明确的步骤,例如药品研发测试的阶段I、阶段II和阶段III。在其他部门,规划产品的研发不受监管要求的影响,因此结构上不那么有序。例如,规划活动可能只与企业的决策一致,这些决策包括在新的地理市场开设生产设施,或者让具有不同属性的新产品进入市场。在这些情况下,潜在的新产品可能不太容易被竞争对手发现,但它仍然可以是反垄断分析的核心。在某一特定地区,如果很难识别那些有规划产品的企业,就会产生进一步的不确定性。
涉及规划产品的一些案例有一个显著特征,例如当新产品是现有产品的“下一代”版本时,它们与现有产品市场的联系相对更容易,也更直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依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但评估拟合并的竞争影响相对就比较容易。当某些定义明确的规划产品以一组现有产品为目标时,用于评估现有产品市场竞争的分析技术常常可以移用于评估涉及这些规划产品的合并。
规划产品剩余的“上市时间”是竞争分析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与规划产品相关的大部分研发成本已经产生,并且新产品的发布(在没有合并的情况下)即将到来,那么对竞争的关注与现有产品重叠引起的关注非常相似。在实践中的一个区别是:缺乏关于新产品需求的真实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关注的是由于其中一家企业拥有的规划产品与其合并对象拥有的现有产品(或多个产品)之间的竞争被消除而产生的单边价格效应。此时,由于大部分或全部的研发成本已经产生,停止规划产品的研发这一单边创新效应问题往往不会出现。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合并后的企业可能会压缩产品,但与此同时,合并后的企业可能会放弃已经推出的产品。如果合并导致上述情况发生,由于产品种类的减少和剩余产品的竞争压力减弱,消费者通常会受到损害。
如果规划产品离成功的商业化还比较远,而且在产品可以上市之前还必须付出巨大的研发成本,那就更有可能产生单边创新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合并与否,产品引入的成功概率是分析的核心部分。对创新的损害可能是由于合并后的企业对特定规划项目投入的资源减少,或者是由于减少了将要投资的规划项目数量。
当我们转而讨论在实践中出现的不同事实模式时,对与规划产品相关的基本竞争问题进行分类是有帮助的。第一,合并可能降低规划产品成功引入的概率。创新的减少会减少产品的多样性,并在未来降低其他产品的竞争压力,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第二,合并可能会推迟规划产品的发布,产生同样的反竞争效应,只是没有那么显著。第三,在合并后,即使规划产品得到成功研发,未来的产品市场竞争也可能不会那么激烈,因为合并带来了竞争产品的共同所有权。
3.1.1现有产品和规划产品的重叠
当一家拥有现有产品的企业与正在研发其替代品的竞争对手合并时,现有产品和规划产品的重叠就出现了。正如第2节解释的,这种类型的合并使业务窃取效应内部化,因为规划产品的成功商业化将转移现有产品的盈利性销售。因此,在其他情况不变时,合并将降低投资于新产品并将其引入市场的激励。如果现有产品和规划产品是近似替代品(即它们满足相似的消费者需求),而且从现有产品转移到规划产品的销售有很高的利润率,那么业务窃取效应会更大。如果现有产品市场高度集中,而且规划产品是现有产品未来竞争的主要来源之一,那么销售的转移率和利润率很可能都非常高。
如果规划的研发过程基本上是确定的,也就是说,如果关于规划产品盈利能力的大部分不确定性已经解决,那么合并可能会导致合并后的企业直接放弃研发工作。如果合并前引入产品的净增利润超过(剩余的)研发成本,但合并后由于业务窃取效应的内部化而使净增利润低于(剩余的)研发成本,那么“杀手型合并”就有可能发生。根据相关学者(Gilbert and Newbery,1982)指出的标准的垄断抢占效应,“杀手型合并”可能对买卖双方都有利。如果规划产品对现有产品构成了严重威胁,那么在位企业购买规划产品并将其取消的激励非常强。如果另一家企业发出了将要收购该规划产品并大量投资于研发的可信信号,就会加剧规划产品对现有产品的威胁。另外,即使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即合并后的企业会立即推出规划产品,消费者仍然会受到传统单边价格效应的损害。
如果规划的研发过程是随机的,而且研发的成功概率取决于研发投资的水平(这经常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假设),业务窃取效应内部化通常就会导致合并后的企业减少其研发工作,从而降低产品研发成功的可能性。在这种事实模式下,消费者的预期损害源于引入新产品或创新产品的较低可能性,以及成功引入新产品时新产品与现有产品之间价格竞争的缺失。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合并导致的竞争减少取决于将业务窃取效应内部化的强度。重要的核心目标是,在没有合并时,从现有产品转向新产品的预期销售的盈利能力。评估这种转移效应时,可以考虑现有产品的当前盈利能力和未来盈利能力、现有产品和规划产品之间的近似程度以及这两种产品在市场上重叠的预期持续时间。如果现有产品受专利保护,那么专利保护的剩余期限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果规划产品会在现有产品仍享有长期的有效专利保护之时进入市场,则更有可能产生显著的转移效应。(*30.Cunningham et al.(2019)发现,有证据表明,如果合并后的企业可做的选择更少(意味着拟合并企业的产品是密切的竞争对手),而且如果合并后的企业现有产品的剩余专利期限更长,就有更高的概率中断规划中的药品研发。)
正如第2.3节讨论的,规划产品与现有产品之间的业务窃取效应内部化会对消费者产生不利影响,衡量该影响需要基于知识溢出内部化和/或存在可知的研发协同效应可能带来的竞争效应。例如,如果合并能够提高研发活动的效率,合并后的企业就更有可能对规划产品进行研发。
3.1.2规划产品之间的重叠
当两家拟合并企业都拥有仍在研发的产品时,就会出现规划产品之间的重叠。其损害竞争的原理与现有产品和规划产品的重叠类似。关键的区别在于,业务窃取效应只适用于尚未上市的未来产品。这使得被转移的销售价值更难估计,因此转移效应的大小也更难估计。这并不是说与规划产品之间的重叠相关的创新问题在重要性上不如与规划产品和现有产品重叠相关的创新问题。相反,由规划产品之间的竞争导致的业务窃取效应可能会特别强烈,因为一种新的创新产品在未来可能会比现有产品获得更高的利润,使得业务窃取效应的内部化更加强烈。(*31.在Federico et al.(2018)包含了随机产品创新的横向合并模型中,相较于合并对手不创新(即现有产品和规划产品重叠)的情况,在合并对手成功创新(即规划产品之间重叠)的情况下,两家拟合并企业的创新激励会下降更多。也就是说,当拟合并企业中的一家“追赶上”另一家提供的(新)创新产品时,相对于它“避免”了与另一家企业的旧产品或现有产品相互竞争的情况,合并会导致每家合并企业的创新激励减弱。值得注意的是,合并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减弱创新激励,所以竞争和创新之间不存在倒U形关系;参见第2.4小节的讨论。)在这些情况下,评估损害方面的困难不是概念上的,而是十分具体的:我们很难有把握地预测将引进哪些规划产品、何时引进以及它们将如何竞争。这些产品等待上市的时间越长,需要证明的这些具体问题就越难以处理。
3.1.3处理产品研发的不确定性
在评估与规划产品有关的竞争性重叠(competitive overlap)时,一个反复出现的挑战是如何处理不确定性的作用。在某些行业,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如果没有合并,成功引进单个规划产品的平均概率可能相对较低(例如低于50%)。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评估那些更有可能不会出现的竞争性重叠。这个问题对于研发竞争的反垄断评估至关重要,因为不确定性是研发的一个基本特征,特别是那些处于研发规划早期的项目。
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适用消费者福利标准就意味着,当合并会导致因竞争减少造成的预期消费者福利下降时,执法当局应进行干预。也就是说,执法当局应当比较合并与未合并时消费者福利的预期现值。这意味着,即使规划产品在没有合并的情况下被引入的可能性很低,只要新产品对消费者的价值很高,合并也可能是反竞争的。(*32.这是英国财政部委托撰写的报告(“Unlocking Digital Competition,Report of the Digital Competition Expert Panel”,2019年3月)中提出的路径,该路径符合“损害平衡”法(第3.88—3.100段)。报告特别指出:“仅仅质疑合并目标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那些合并,将是过分谨慎之举。”(第13页)类似的讨论可以参见Bourreau and de Streele(2019)的研究。)
我们现在使用一个包含规划产品研发不确定性的简单模型来说明这些要点。假设A公司有一个规划项目,该项目在不发生合并时的成功概率为pA。如果项目成功,就会与B公司的现有产品形成竞争。此时的消费者剩余为SAB。或者,如果A公司的规划项目失败,那么消费者剩余就是SB,其中SB
与合并后的预期消费者剩余相比,会如何呢?如果合并后的公司由于与创新相关的业务窃取效应内部化而简单地扼杀A公司的规划项目,就会出现最简单的情况。此时,合并之后的预期消费者剩余就是SB,所以合并将预期消费者剩余降低了pA(SAB-SB)。合并剥夺了消费者享受A公司成功研发产品带来的好处。pA即使相对较小,也会对消费者造成显著损害。如果消费者从A公司的成功研发中显著受益,即产品种类更多和价格竞争更激烈,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在本例中,对竞争性重叠的概率适用了“宁信其有”的标准,倾向于允许有害的合并继续进行,尤其是在目标公司正从事一个相对不太可能成功的项目,但项目如果成功将产生巨大利益的时候。实际上,只要收购完成得足够早,从而被收购项目失败的可能性仍然大于成功的可能性,这种方法就允许在位企业收购一个敢于冒险的颠覆性项目。(*33.此外,正如我们下面讨论的,现有的研发项目往往代表了企业的能力,因而可能只是未来许多可能的竞争性产品中最突出例子。)这种政策不会保护竞争和消费者,而会抑制创新和破坏。(*34.在专利有效性不确定的情况下,类似的讨论也适用于专利权人和挑战者之间的专利和解。美国和欧洲的法院都发现,如果合并协议消除了专利权人和挑战者之间的竞争风险,就有可能是反竞争的(例如FTC 诉Actavis Inc.,133 S.Ct.2223,2013年;European General Court,Lundbeck诉Commission案的判决,T-472/13号案件,2016年9月;European General Court,Servier诉Commission案的判决,T-691/14号案件,2018年12月)。在此类协议没有可能的反事实情景下(由于专利有效性的不确定),这些法律判决与适用预期消费者福利标准是一致的。关于预期消费者福利标准适用于专利协议的正式讨论,参见Shapiro(2003)。)
即使合并后的企业将继续积极努力地追求目标公司的规划项目,还是会出现同样的结果:即使目标规划产品相对不太可能被引进,合并也会损害竞争和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合并不会使消费者体验到的产品种类减少,但是他们仍然会丧失B公司现有产品和A公司新产品进行市场竞争带来的好处。
如果合并将重要的知识溢出效应内部化或导致研发协同效应,涉及不确定的规划产品的合并评估自然会变得更加复杂。如果合并给特定的规划项目带来效率,就可以将这些效率合并到上文列出的消费者剩余表达式中。例如,合并可能提高规划产品的质量或者使之更有可能研发成功。理论上,这些影响可以抵消合并可能带来的预期消费者福利损失。
在实践中,反垄断执法机构无法衡量合并之前的预期消费者剩余,也无法将它与合并后的预期消费者剩余进行比较。然而,通过比较与创新相关的业务窃取效应内部化和合并专有的效率,就可以使用合适的代理性证据识别最有可能损害消费者的合并。如果某些关键参数存在不确定性,可以适用错误成本框架。该框架将力求平衡执行不足的预期成本(例如,在没有合并就发生重叠时对消费者的预期损害)和过度执行的预期成本(例如,消费者从先前合并带来的效率中获得的预期收益)。(*35.Katz and Shelanski(2005)提倡在这种情况下使用错误成本框架。有关数字市场背景下的讨论,参见Cremer et al.(2019)。)
在评估合并对预期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时,可能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合并控制政策是否会降低“进入式收购”的盈利性,从而影响高成本研发的事前盈利性。我们将在下文讨论一个案例时强调这一点,在该案例中,一家大型在位企业试图收购一家具有潜在颠覆性能力的小企业。
3.1.4对规划产品重叠的救济
现在,我们转而讨论如何为规划产品重叠制定适当的结构性救济措施。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合并都是通过合并企业的资产剥离实现的。因此,对合并控制的整体有效性而言,救济措施的设计是核心。
对规划产品重叠的适当救济取决于两家合并企业之间更广泛的竞争互动的性质。如果规划产品重叠与两家企业上游研发能力的重叠没有关联,那么专门针对规划产品重叠的救济措施可能足以避免对竞争的损害。
如果在某个特定领域有许多研发竞争对手,然而由于研发的随机性,两家拟合并企业是少数在市场和研发规划中有特定产品的企业,因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高度集中的市场中有可能出现竞争性重叠,这种情况就可以作为代表性案例。在这种情况下,两家拟合并企业之间有问题的重叠仅仅反映了随机研发过程的事后实现。此时,旨在维护重叠领域竞争的针对性救济措施可能就足够了,因为在这种假设的情况下,有许多研发竞争对手,在没有发生合并时,另一个这种重叠就不太可能很快出现。例如,在现有产品和规划产品重叠的情形中,只要第三方有足够的规模和能力继续研发规划产品并使之上市,一个合适的救济措施可能包含将资产从合并后的企业剥离到第三方,而这些资产要包括规划产品以及允许其进一步发展和商业化所需的资产。或者,现有产品可能被剥离,而这同样会维持现有产品和规划产品之间的竞争。如果合并涉及一个拥有规划项目的单产品竞争者(single\|product competitor),这种针对性救济措施也可能是有意义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剥离规划产品就相当于阻止交易。
如果合并造成的规划产品重叠反映了作为基础的上游研发能力之间更广泛的重叠,那么合理的救济方案就会复杂得多。此时,简单地剥离重叠领域的一种产品,可能不足以阻止未来合并带来的竞争削弱。下文会回到这个问题。
3.1.5案例研究
竞争当局通常会评估涉及规划产品的合并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些案例通常涉及有明确研发流程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上,可以相对简单地识别规划产品造成的竞争重叠。美国和欧盟的竞争当局审查过几起涉及制药和医疗设备的此类案件。美国新近的例子包括Thoratec/Heartware合并案,该合并在2009年被联邦贸易委员会阻止;2017年的Mallinckrodt案,在该案中,联邦贸易委员会认定Mallinckrodt对一个药品研发项目的收购抑制了竞争,因为该研发项目本来可以与该公司利润丰厚的现有产品竞争。
欧盟新近的案例包括美敦力/Covidien合并案(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医疗设备制造商的合并)、辉瑞/Hospira合并案(涉及生物仿制药的重叠)和诺华/葛兰素史克(肿瘤业务)合并案(涉及创新性癌症治疗药研发阶段的重叠)。与研发规划或产品规划相关的案例不局限于制药和医疗设备部门。在欧洲,一个与规划产品相关的著名案例就是通用电气/Alstom合并案,该案涉及大型燃气发电轮机。(附录B更详细地讨论了美国和欧洲最近涉及规划产品的一些合并案例,并包含了与救济方案相关的问题。)
3.2能力重叠
引发创新担忧的第二类广义合并包含了研发能力相互竞争的企业之间的合并。我们在此指的是,合并涉及的企业拥有一系列面向某些相似的创新领域或研发阶段的资产。这些资产可能包括新产品和新流程的有效发现;研发和商业化所需的一些要素;知识产权;技术获得;人力资本,比如工作熟练的科学家或工程师;研发设施,比如实验室、专业设备等;专业化监管、分销和商业化资产;无形资产,比如客户的业绩记录等;以及可以进行新技术升级的既有客户。在发现和推出新产品和改进产品方面,这些资产往往使某些公司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
一般而言,这类案例中的损害原理符合美国《横向合并指南》中关于创新和产品多样性的一个具体问题,即如果没有发生合并,这两家企业在创新能力上的重叠会使它们在相似的领域推出新的创新产品,并在相应的产品市场上展开竞争,从而相互抢夺利润丰厚的销售量。行业中如果有一些具有竞争创新能力的企业,其中两家企业的合并将使这些业务窃取效应内部化。合并可能弱化在重叠的研发领域启动新研发的激励,剥夺消费者从这些领域的未来产品市场竞争中获得的一些好处。根据我们在第2节中解释的一般原理,由于合并和/或合并带来的研发协同效应会提高有利于竞争的独占效应,从而抵消上述这些问题。
研发能力重叠的企业之间合并,自然也可能涉及研发和产品上市阶段的明确重叠。例如,在任何时候,两家在某种杀虫剂上具有强大能力的农用化学品企业可能在特定杀虫剂产品上存在实际产品和规划产品的重叠。能力重叠很可能与可观察到的现有产品和规划产品的重叠密切相关,尤其是如果相关能力长期存在、研发规划的寿命足够长,以及产品的平均商业寿命也很长。在这些情况下,被观察到的潜在能力重叠会表现为在一个或多个现有产品或者规划产品上的重叠。但是,原则上,考虑到研发的随机性,在评估特定的合并时,这些潜在重叠即使尚未导致规划产品或现有产品出现可观察到的重叠,有重叠创新能力的两家企业合并也会引发担忧。其中的可能性需要具体个案具体评估。
在考虑合并双方的能力重叠时,尤其是考虑与研发相关的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时,需要一个广泛的视角。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竞争能力的企业很可能会参与研发项目组合。因此,它们在未来“相互碰撞”进而产生业务窃取效应的可能性会高于任何单个项目成功的可能性。
在能力重叠的情况下,大多数合并审查不太可能获得创新转移效应的量化估计。但是,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替代性证据(proxy),以证明创新能力重叠的企业合并会产生重要的业务窃取效应。一个自然要考虑之处是已有产品和规划产品重叠的重要性和频率。如果相关重叠领域的创新能力可长期持续,这些信息可能就特别有用。类似地,对于基础研发能力重叠而言,关于现有产品和规划产品重叠或者规划产品之间重叠的证据可能是一个有用的替代性证据。关于专利组合重叠的证据也可以是竞争能力的有用指标,尤其是如果可以控制专利的质量(例如,考虑专利引用),并且如果可以识别与特定专利类别相关的特定研发轨迹。鉴于能力重叠可能引发的竞争问题是中长期的,证明进入壁垒显著而持久的证据可能与竞争评估的关联度很高。考虑到将能力重叠与特定的现有产品市场联系起来和预测未知产品的需求存在固有困难,对能力重叠的评估不可避免地要关注未来产品潜在市场的供给侧而不是需求侧。(*36.参见Gilbert and Sunshine(1995),以及Katz and Shelanski(2005)。)
美国和欧洲的竞争监管当局在指南中认识到了对能力重叠进行审查的必要性。例如最近修订的美国司法部/联邦贸易委员会《知识产权许可的反垄断指南》(2017年1月)提到了“研发市场”。(*37.“研发市场”这个术语取代了之前的“创新市场”。知识产权许可指南对研发市场的定义如下:“一个研发市场的资产包括由研发构成的资产,其中的研发与商业化的产品有关或者是以特定的新产品或被改进产品或过程为目的,以及包括研发的近似替代品。当研发以特定的新产品或被改进产品或过程为目的时,近似替代品可能包括研发工作、技术和产品。比如,通过限制一个虚构垄断者的能力和动机来降低研发速度,这些研发工作、技术和产品显著约束市场势力在研发中的作用。只有从事相关研发的能力会与特定公司的专门资产或特征相联系时,当局才需要划定研发市场。”(第10—11页))该指南表明,在相关的研发市场上,如果至少有另外四个竞争者,那么同一研发市场内的两家公司(在创新能力上相互竞争的公司)成立合资企业不太可能是反竞争的。同样,欧盟委员会2011年的《横向合并指南》表明,研发合作可能会影响创新和新产品市场的竞争。这些指南表明,在创新过程有良好结构的情况下,比如在制药行业,有可能识别相互竞争的研发“极”,并评估是否还有足够数量的研发“极”和横向研发协议的各方。(*38.参见2011年1月的欧盟委员会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第119—120段。)在分析上,这种方法类似于一个研究创新能力的框架,以确定能力重叠的两家公司合并是否有可能在特定的研发轨迹上阻碍创新,或者更广义地说,减少未来创新产品的竞争。
如果在某个领域有创新能力的两家公司合并,会导致反竞争的能力重叠。适当的救济方案对这种合并来说可能特别微妙。正如上文解释的,有问题的能力重叠很可能与一个或多个现有产品重叠或者规划产品重叠共存,并且前者确实是后者的原因。在此情况下,出现有问题的重叠可能反映了未来再次发生这种重叠的高度可能性,尤其是在很少有公司具备必要的能力时。
在以上情形中,仅针对现有产品和规划产品重叠的救济措施,不足以抵消合并对创新造成的中长期损害。只解决现有产品和规划产品的重叠,会在短期和中期缓解合并带来的损害,但不太可能解决在更广泛领域内失去实际创新者造成的长期损害。这样的救济措施就像是在应对竞争的可见症状,而不是应对潜在的驱动因素。相反,适当的结构性救济措施将要求剥离更广泛的资产以及重叠的现有产品和规划产品,包括适当的“上游”创新能力。这可能包括剥离合并企业之一的研发机构、其技术和知识产权资产、专门的人力资本以及获取现有客户的机会等。然而,考虑到一个研发组织的脆弱性,“分拆”复杂的现有结构,或者把两个合并企业的资产放在一起的“混搭”方案,都可能削弱结构性救济措施的有效性。因此,通过资产剥离解决创新能力的重叠可能要复杂得多,而且需要剥离的资产也相应地更多,然后才能救济特定产品或规划产品的重叠。
美国和欧盟的竞争监管当局介入了许多涉及创新能力的重要案件,致使要么合并被放弃,要么大量资产被剥离。这些案件涉及广泛的部门,包括费率测算服务(rate\|measurement services)、证券交易所、农用化学品、半导体制造和油田服务。这些案件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所在行业都有持续的高成本创新、高进入壁垒以及实际创新者寥寥无几的特征。在竞争监管当局接受补救措施的这些案件中,通常包含剥离重要的创新能力(除了出售特定产品或规划项目外),以弥补合并造成的独立创新者的损失。正如这些案件表明的,在合并对手具有重大且竞争性创新能力的合并中,即使没有适当的结构性救济措施,其设计可能也特别困难。(附录B回顾了美国和欧盟近期涉及创新能力的一些比较突出的合并案例。)
3.3支配型企业对潜在竞争对手的收购
我们考虑的第三类合并是由一家支配型企业对一家小企业的收购,其中这家小公司的市场份额要小得多,但它有创新的能力,从而可以在未来从支配型企业“窃取”重要且利润丰厚的业务。第三类案例尤其适用于数字行业,包括谷歌、脸书、苹果和微软在内的一些大型在位平台近年来收购了许多规模较小的企业。
当一家支配型企业试图收购一家在邻近市场上有强大能力的目标企业时,所需的分析与前面讨论的事实模式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我们可以设想,目标企业拥有一个规划项目,即开发自己核心产品的增强版本,并且有能力开发可以与支配型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相竞争的产品。然而,实际上,目标企业的产品还不能很好地替代在位企业的产品,而且人们不太可能由于观察到已有产品或规划产品重叠就认为存在能力重叠。实际上,合并双方可能会辩称,合并根本就不是横向的,而且由于固有的不确定性,关于未来产品可能重叠的证据也许是模糊不清的。
支配型在位企业收购潜在竞争对手的案件中,最清晰的损害理论是,收购将消除在位企业面临的威胁,使之得以保护在市场中的现有租金。这种情况可能会损害消费者,原因在于消费者直接损失了目标企业提供的创新产品,同时在位企业的竞争压力降低。换句话说,这种类型的收购不仅会导致市场失去破坏性的进入者,还会对在位企业的创新激励产生连锁效应,因为合并后的未来销售额会无可争议地减少。(*39.在具有网络效应这样的显著先发优势特征的市场中,以及在创新竞争具有专利竞争特征的市场中,对在位企业创新激励的间接影响很可能非常显著。)
在实践中,发展这种损害理论的主要挑战往往是证据。由于没有具体的规划产品重叠,也许很难证明被收购企业很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窃取”在位企业的业务。类似地,如果缺乏在位企业和目标企业在已有产品和规划产品上相竞争的证据,就很难找到合适的替代性证据来证明能力重叠。这个困难可能在全新且快速发展的数字市场中尤为突出。在这些市场中,难以准确地确定哪些能力是成为有效的创新者和竞争者必需的,而且其他未合并的公司可能也会为了未来的销售展开可信的竞争。
脸书在2012年对照片墙(Instagram)的收购很好地说明了这些问题。(*40.关于本案件的更多讨论,参见Baker(2019,第160—163页)。)在合并时,脸书将照片墙形容为一个补充:脸书发布文本,而照片墙处理图片。(*41.然而,至少有的Facebook内部人士将Instagram视为威胁,参见https://nypost.com/2019/02/26/facebook-boasted-of-buying-instagram-to-kill-the-competition-sources。)事实上,现在脸书上使用的图片比以前更多。事后看,人们很容易想象照片墙本来会发展成为一个受欢迎的社交媒体网站,并与脸书展开实质性的直接竞争。然而,这种预测的不确定性很高。在合并时,由于照片墙缺乏过去的业绩和收入,将它归类为具有威胁性的取代者,在证据上面临挑战。从合并被批准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照片墙如果没有被合并会如何发展。
另一个启发性的案例就是沃尔玛2016年对Jet.com的收购。Jet.com是少数几个有能力与亚马逊竞争的在线零售网站之一,后来被沃尔玛收购。我们可以观察沃尔玛在收购Jet.com后做了什么,但我们无法观察两家企业没有合并时,Jet.com原本会做什么。换句话说:在收购之时,Jet.com主要是沃尔玛实体店的线上补充,从而使沃尔玛能够提供与亚马逊竞争的创新零售服务,还是说Jet.com主要是沃尔玛的竞争对手?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关于零售业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都是巨大的,而Jet.com在未来几年与亚马逊或沃尔玛竞争的独立能力同样是未知的。
当提出这类交易时,使用滑动尺度(sliding scale)可以帮助处理固有的不确定性。比较上述两个例子,如果脸书在社交媒体上的市场势力比沃尔玛在零售上的市场势力更强或者更持久,那么社交媒体行业的破坏可能性即使很小,对消费者也会更有价值,因为比起相同可能性的破坏性创新在零售业的作用,社交媒体行业的破坏将产生更多的创新和产品市场竞争。
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一个合适的方法是采用错误成本方法(如前文的讨论)研究合并对预期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执法不力的成本是在位企业市场势力的程度和持续时间的函数,即因失去来自目标企业的竞争而损失的价值。如果在位企业存在竞争者,或者存在比目标企业更好的潜在竞争者,那么潜在竞争来源的损失可能就是有限的。然而,如果“市场中的竞争”是有限的,而且主要或唯一的竞争是“为了获得市场的竞争”,那么损失潜在挑战者可能会极大地损害消费者,从而增加执法不力的成本。
还有另外两种有用的方法可用来评估对新生竞争对手的收购。第一种方法是分析决定收购价格的因素,以深入了解支配型在位企业到底是与目标企业共享垄断租金,还是与目标企业共享预期协同效应的价值。(*42.关于该方法的阐述,参见Mallinckrodt(2017)在附录B以及CDK/Auto-Mate(2018)对联邦贸易委员会干预的介绍。)第二种方法是审查支配型在位企业以前的收购行为,以确定该企业到底是有收购潜在竞争对手的模式,还是有通过类似收购获得巨大协同效应的历史记录。
过度执法的成本取决于是否存在合并专有的效率。当一家在位企业收购一家小型目标企业时,可能的合并专有效率包括两家企业科技能力的协同效应,比如将大企业的技能和协议应用到被收购企业的产品上,或者改善两种产品合作的能力。协同效应可以增加目标企业的产品成功上市的可能性,或者提高其上市的速度。一家支配型企业或许能够证明,它在此前的类似收购中成功地获得过这种效率。
这些交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合并专有效率的评估到底是与目标企业仍然是独立竞争对手时的情况相比较,还是与目标企业被另一家利润不受其威胁的(较大)企业收购时的情况相比较。基于替代交易的审查类似于目前针对“失败企业”的审查,否则将不适用。(*43.参见美国《横向合并指南》第11章“Failure and Exiting Assets”。)即使在许多情况下反垄断当局很难确定具体的“其他情况下的”收购以实现更严厉的执法,这种更严格的审查也将使天平向更严厉的执法倾斜。(*44.关于对这一点的具体建议,参见英国财政部委托撰写的Furman Report(Unlocking Digital Competition,Report of the Digital Competition Expert Panel,2019年3月),第96—97页。如果拟议的合并是在激烈竞争之后才实现了对目标企业的收购,那么其他收购者可能更容易被识别。关于合并中其他反事实(包括可识别其他收购者的具体案例)的讨论,参见Amelio et al.(2018)。)
在处理支配型在位企业对小公司的收购时,另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被收购后的前景能否为小企业开展创新提供重要的事前激励,也就是所谓的“并购式投资”(investment for buyout)。虽然阻止支配型在位企业的所有收购行为的过严政策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如果合并执法政策着重于保护竞争过程,而且确实忽视了对“并购式进入”(entry for buyout)的一般影响,那么这种合并执法政策将推动真正的创新,原因至少有三个。第一,这种政策会阻止风险资本和其他资本推进从一开始就是为反竞争收购而设计的类似项目,并将鼓励更多有益于社会的创新。(*45.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参见Cunningham et al.(2019)。这篇文章还提供了证据,以证明在制药行业中,合并不会导致目标企业人力资本的有效重新配置,并且在收购前的投资者中,只有22%会在合并后继续投资收购方。)第二,这种政策将随着时间推移削弱在位企业的市场势力,从而增强在互补品供给方面进行创新的激励。第三,在合并之后,如果在位企业直接关闭或减少对竞争性创新的投资,此时“并购式投资”的收益最终也不会惠及消费者,那就没有权衡可言。(*46.最近的正式工作包含“并购式投资”效应,不支持对横向合并施行宽松政策。Mermelstein et al.(即将发表)构建了一个动态的同质品双寡头古诺竞争模型,该模型囊括了对市场进入者进行并购式投资的激励。他们发现,从消费者福利的角度看,最优的合并控制政策相当于不允许合并的严格静态政策。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好处之一在于阻止了低效率的并购式投资。Igami and Uetake(2019)考虑了一个合并和创新的动态寡头模型,将之调整并应用到了硬盘驱动行业。在他们的模型中,合并控制导致了(a)企业的事前进入和生存,(b)事后减少创新和竞争之间的权衡。他们的模拟表明,相对严格的合并政策是可取的:在这些模拟中,尽管大多数好处来自阻止使竞争者数量少于3家的合并,但是,使公司数量少于6家的合并就会减少消费者福利。更一般地说,在许多标准经济学模型中,合并降低了创新激励,但对拟合并企业来说是有利可图的(见附录A)。因此,合并允许潜在竞争者与支配型企业合并从而锁定更高的租金(与相反的情形相比),这个事实并不促进创新。相反,在位企业和挑战者可能就是利用这种手段分享市场势力带来的租金。)对在位企业针对小企业的反竞争收购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将与保护破坏性市场进入者免遭排他行为影响的政策一起发挥作用(这是我们的下一个话题),并通过增加未来销售的可竞争性提高进入者的预期利润,从而促进创新。
4.支配型企业在创新行业的排他行为
现在我们转向创新产业中的支配型企业,讨论对其商业行为的反垄断处理。我们不会讨论企业是不是占支配地位的问题,而只是关注其行为。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支配型企业通过排除实际竞争对手或者潜在竞争对手从而有可能阻碍创新的商业行为。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在动态的创新市场中,支配型企业采用了反竞争的商业行为,以排除令其讨厌的新兴企业或潜在进入者,它们都是常见的破坏性市场主体。如果这些行为阻止了新型和改进型产品及服务的出现或成功,消费者就会受到损害。在支配型企业向消费者免费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中,这些新型和改进型产品与服务是消费者剩余的重要来源,这在数字市场中很常见。
当一家支配型企业拒绝将其产品卖给与其竞争对手交易的消费者时,就是排他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例如,在大约70年前的美国俄亥俄州洛兰市,支配型地方报企面临一种激动人心的颠覆性技术,即地方广播电台的竞争,这家报企拒绝接受那些在地方广播电台投放广告的人在报纸投放广告。最高法院判决这种行为违反了《谢尔曼法案》第2条。(*47.Lorain Journal 诉United States,342 U.S.143 (1951).)
我们使用广义的“排他行为”这一术语,既包括阻碍竞争对手进入(或诱导其退出)的行为,也包括削弱竞争对手实际竞争能力的行为。(*48. 然而,即使这种行为会产生将竞争对手逐出市场的效果,我们使用的“排他行为”一词也不包含基于优胜的竞争,例如,当支配型企业提供改进型产品和服务时。)例如,排他行为可以增加竞争对手的成本,降低其产品质量,或者妨碍其获得重要的投入品或消费者。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最近对高通公司提起了诉讼,该案提供了一个可能损害创新的排他行为的例子。(*49.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诉Qualcomm,Case No.17-CV-02200-LHK,美国加州北部地区法院。本文作者之一夏皮罗在本案中为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供了证词。)联邦贸易委员会宣称,高通公司的某些商业行为提高了高通公司竞争对手销售调制解调器芯片的成本,从而降低了竞争对手投资研发新一代调制解调器芯片的激励。联邦贸易委员会由此认为,高通公司通过提高竞争对手的成本损害了竞争,巩固了高通的支配地位。尽管高通在现代芯片上的一些竞争对手,尤其是英特尔,投入了大量研发资金开发新型和改进型现代芯片,联邦贸易委员会还是做出了上述指控。正如下文强调的,对经济影响的评估需要将实际结果与一个适当的反事实结果进行比较,而该结果反映了在没有被指控的行为时(不确定的)研发、投资、价格和市场进入路径。2019年5月,负责审理联邦贸易委员会案件的法官做出判决,高通的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
4.1建立适当的反事实
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高通的案例说明,反垄断案件涉及可能损害创新的商业行为时,有一个常见特征,就是从经验上确定这些行为如何影响产业发展可能很困难,尤其是如果法院要寻求没有反竞争行为时会产生何种创新的确凿证据。
要了解问题的本质,首先考虑这样一个例子,即一家公司销售一种专利药,向一家仿制药企支付一大笔钱,使之同意在一段时间内不向市场提供该药品的仿制药。在这类“付费推迟”案例中,通常有大量证据表明,仿制药的进入会导致药品价格大幅下跌。利用这些证据,可以量化仿制药延迟进入市场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害。的确,在仿制药实际延迟进入的情况下,可以相当准确地估计仿制药延迟进入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考虑如下情形:一家支配型在位企业阻碍了竞争对手对研发的投资,或者阻碍了竞争对手开发或推出新产品。在这种案例下,通常不可能量化对客户造成的损害。的确,由于新产品开发及其市场接受情况固有的不确定性,通常不可能知道,本来会开发出什么样的新产品和创新产品,会在什么时候推出这些产品,或者这些产品会有多受欢迎。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认定一家支配型企业的行为损害了创新并因而违反了反垄断法所需的大量证据是竞争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一套更坚定明确的反垄断制度会发现,当受到质疑的行为阻碍竞争对手的创新激励或能力,因而扰乱了竞争过程时,就会出现违规行为。这是合理的,因为经济学家明白,当某项活动(如研发投资)的激励减弱时,就可以预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减少这项活动。因此,如果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开发新产品的激励减弱了,那就可以有把握地得出创新将会减少的结论。更谨慎的反垄断政策会要求证据,以证明由于支配型企业那些受到质疑的行为,竞争对手实际上减少了对特定项目的研发,以及由于某些特定产品没有开发出来,研发的减少损害了消费者。在许多动态市场中,要证明这些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举证责任设置过高,那么在动态和创新的行业中,反垄断执法就会效率低下。
这些行业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与长期技术趋势的影响相关的逻辑谬误。在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方面,高科技市场有着强大的长期趋势(质量可以是速度或内存容量这样的产品属性)。被告有时将这些市场改进(更便宜和更快速的产品)作为证据,证明没有出现排他行为。然而,正确的问题是,在没有排他行为的情况下,速度是否会提高得更快,价格是否会下降得更多。一个行业经历了技术进步,随着时间推移,产品不断改进且产量不断增加,如果这个事实与排他行为的存在不一致,那么,如果不放弃高科技行业的反垄断执法,就会严重阻碍该行业。
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高通公司的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政策权衡。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交的证据显示,即使智能手机制造商生产和销售的智能手机含有非高通的调制解调器芯片,高通受质疑的行为也使之能够从智能手机制造商那里获得不合理的高额专利使用费。(*50高通已经承诺以合理的条件许可其基本标准专利。)联邦贸易委员会解释说,这些过高的专利使用费实际上增加了高通竞争对手的成本,从而阻碍了它们进行必要的研发投资,以开发新型和改进型现代芯片。这个结论来自产品开发的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如果一家企业考虑投资开发一种新产品,但是预期自己的销售量和利润率都会减少,那么不可避免地,它开发新产品的激励就会降低。作为回应,高通辩称,联邦贸易委员会没有证明,具体的调制解调器芯片供应商退出市场或削减研发投入的原因就是高通受质疑的行为。要求政府执法机构提供这类证据,以作为确立违法行为的先决条件,将大大削弱反垄断执法在动态的创新产业中的作用。(*51.相比之下,如果一家私人企业正在寻求反垄断损害赔偿,一些额外的因果关系证据将是重要的。)
反垄断执法者、经济学家和法院早就认识到,即使存在反竞争的垄断或其他有害行为,价格也会下降且产品可以改进。1998年美国司法部起诉微软的垄断案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在与英特尔兼容的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52.Findings of Fact,United States v.Microsoft Corporation,Civil Actions Nos.98-1232 and 98-1233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District of Columbia,November 5,1999),第33—34页。)微软推出了创新产品,该产品的基础是前几代软件,其中包括Windows 95,它提供的用户界面“受到了消费者前所未有的欢迎”。(*53.同上,第8页。)但是,这些革新虽然对消费者很有价值,但并未排除反竞争行为的危害。政府声称,微软通过消除Netscape和Java带来的竞争威胁,非法地维持其操作系统的垄断地位,对此微软也没有成功地进行辩护。(*54.同上,比如第 66—68页和第409页。)
另一个例子是,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动态和创新的高科技市场出现了多次价格操纵事件。液晶显示屏(用于个人电脑显示器和电视)(*55.U.S.Department of Justice,“LG,Sharp,Chunghwa Agree to Plead Guilty,Pay Total of $585 Million in Fines for Participating in LCD Price-Fixing Conspiracies,” November 12,2008,available at https://www.justice.gov/ archive/opa/pr/2008/November/08-at-1002.html;Plea Agreement,United States v.Hitachi Displays Ltd.,Case No.CR 09-0247 SI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May 26,2009),available at https://www.justice.gov/atr/case-document/plea-agreement-163;Morgan Bettex,“Japan Fines Sharp $3M in LCD Price-Fixing Scheme,” Law 360,December 18,2008,available at https://www.law360.com/articles/80800/;European Commission,“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six LCD panel producers 648 million for price-fixing cartel,”IP/10/1685,December 8,2010,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0-1685_en.htm.)和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供应商均承认非法组成卡特尔,旨在使价格高于竞争水平。(*56.Non Confidential Version of the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9 May 2010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rticle 53 of the EEA Agreement,DRAMs,Case No.COMP/38511 (European Commission,May 19,2010),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38511/38511_1813_5.pdf;U.S.Department of Justice,“Samsung Agrees to Plead Guilty and to Pay $300 Million Criminal Fine for Role in Price Fixing Conspiracy,” October 13,2005,available at https://www.justice.gov/archive/atr/public/press_releases/2005/212002.htm.)高科技市场显然也不能幸免于反竞争行为。
这些产品——Windows操作系统、液晶显示器和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都是个人计算机的部件。相应地,认为这一时期个人计算机价格的下跌可以证明计算机部件市场不存在反竞争行为,是违背事实的。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经质量调整后的价格指数,个人计算机和相关周边设备的价格在1990年至2010年迅速且越来越快地下降,年均降幅为20.4%。(*57.有关美国劳工统计局和美国经济分析局如何调整个人电脑价格以反映质量的变化,请参见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How BLS Measures Price Change for Personal Computers and Peripheral Equipment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ebruary 23,2018,available at https://www.bls.gov/cpi/factsheets/personal-computers.htm。) 在与个人计算机有关的反竞争行为的后期(1995年以后),个人计算机价格的下降速度实际上比手机和其他高科技产品价格的下降速度还要快。在任何情况下,不管价格下降速度如何,对于评估相关投入品市场中的垄断、合谋和其他反竞争行为造成的损害,这些信息都没什么用。原因在于,损害取决于投入品市场中没有反竞争行为时本来会发生什么。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与适当的反事实进行比较。事实上,由于个人计算机投入品市场存在大量反竞争行为的证据,价格或质量不受影响的结论是不成立的。
正是因为在动态的创新产业中,很难从经验上确定特定商业行为的影响,所以我们通过探索旨在保护竞争过程的反垄断规则来构建分析。这种选择带来了明显的优势:它不必推测反事实情况下的特定发明,同时又可利用经济学理论预测激励和能力变化的影响。总之,我们正在探索反垄断规则,以允许支配型企业通过提供更低的价格和改进后的产品进行竞争,但禁止它们在不向客户提供直接利益的情况下,从事排除破坏性竞争对手的做法。这是美国反垄断法的标准,防止垄断行为就是保护竞争的过程。
我们将分析分为两个主要部分:排除对支配型企业在其核心市场的地位构成威胁的竞争对手,以及排除试图在邻近市场竞争的竞争对手。20年前起诉微软的案件说明了这两种事实模式,以及美国和欧盟的法律手段在一些方面如何不同。美国司法部起诉微软案的焦点是司法部的主张,微软采取了各种做法,以捍卫它在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领域的垄断地位。欧盟委员会指控微软的案件主要基于如下主张:微软试图将其在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方面的垄断权力扩大到邻近市场,即媒体播放器和用于工作组服务器的操作系统。
4.2捍卫支配地位
在讨论具体的商业行为之前,更一般地考虑创新市场中支配型企业的反垄断行为是有指导意义的。西格尔和温斯顿(Segal and Whinston,2007)提出了一种最基本的潜在政策权衡。他们指出,更严格的反垄断政策将以在位企业的利益为代价,增加新进入者的利润。他们随后提出的问题是这种利润转移如何影响创新?其关键点就是,今天的成功进入者可以成长为明天的支配型在位者。事实上,在他们的基本模型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今天的进入者超越了在位企业,与之交换地位而成为明天的在位企业。西格尔和温斯顿在这个模型中,通过改变排除进入者的能力,给出了我们在上文描述的反事实分析。他们指出,“恰恰是在更严格的反垄断执法提高了一项创新在其寿命期内的预期增量贴现利润的时候”(第1707页),促进了创新。同样,甘斯(Gans,2012)认为“静态”分析往往可以给出关于创新的正确答案。
支配型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排除威胁其市场势力的竞争对手。这些方式包括捆绑(如美国微软案)、专卖、忠诚回扣和最惠国条款(MFN)。(*58.附录B提供了两个旨在保护市场势力的排他性策略的例子:最惠国待遇和忠诚度回扣。还有一个支配型平台利用最惠国待遇阻碍商业模式创新的例子,即欧盟委员会对亚马逊在电子书市场上的价格和非价格最惠国待遇的调查。参见欧盟委员会2017年5月4日的决定第9条,以及Buehler et al.(2017)对该案件的讨论。)在平台市场,旨在阻碍市场一方多归属的行为可能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排他性策略。多归属是一种鼓励创新竞争的策略,因为它提高了可竞争性:在多个平台上操作的消费者可以更容易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更具创新的产品上。因此,与传统的专卖安排类似,支配型企业阻碍市场一方多归属的政策可能会对创新产生不利影响。例如,想象一下,如果优步禁止旗下的司机为另一个平台驾驶,会发生什么。由于优步的规模大于来福车(Lyft),优步的规定可能会导致大多数司机只选择优步一家。这将减少来福车可以使用的司机数量,并很可能增加用户在来福车平台上的等待时间,从而降低来福车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从短期看,可竞争性将会下降,因为更多的消费者可能只选择优步,从而来福车平台的创新对消费者来说将不那么明显。此外,如果来福车退出某些地区,优步在这些市场中面临的价格和创新上的竞争压力就会减少。
即使颠覆性的进入者(目前)在效率上低于支配型企业,排除颠覆性的进入者也必定会损害竞争过程。事实上,在受制于显著的规模经济(例如,由于网络效应和/或干中学)的行业,这种模式往往是常态。有些颠覆者最初的效率低于支配型企业,但仍然能够对在位企业构成严重的竞争威胁,因为它们有吸引消费者的对抗性特征,或者它们的效率会随着经验和规模的积累而提高。不管进入者目前的效率水平如何,竞争过程要求他们不应当被实际上的非竞争行为压制,这其中也包括如果没有对竞争者的排他性影响就没有经济意义上的非竞争行为。
在这一领域,有一些最困难和最重要的问题与被控排除新生竞争对手的商业行为有关。由于新生竞争者的成功是高度不确定的,所以只有在它们的成功能带来巨大的竞争价值时,将它们排除出市场才会对预期消费者福利产生很大影响。当在位企业拥有巨大而持久的市场势力时,上述情况最有可能出现。如果消费者的选择有限,那么第二选择实际出现的概率即使很小,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这一观察结果表明,可以使用滑动尺度来评估受质疑的商业行为对竞争的影响:在位企业的市场势力越大且越持久,进入者证明自己应免受排他行为影响所需的成功概率就越低。基本上,这一原则与我们在讨论涉及不确定性的规划产品合并以及支配型企业的潜在挑战者时提出的原则相同(见第3.1.3节和第3.3节)。
基于微软的案件,美国的判例在这一点上是站得住脚的。在政府的诉由中,主题之一便是,Netscape利用Java中间软件对微软的Windows垄断构成了威胁。(*59.参见Bresnahan et al.(2012)从组织的角度回顾了微软案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Shapiro(2009)讨论了微软案中救济措施的失败。)但是这种威胁还没有发展到可以直接替代Windows的地步。在这一关键意义上,Netscape和Java虚拟机为Windows提供了补充,然而对Windows而言只是“新生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上诉法院的结论是,这类竞争受到《谢尔曼法案》的保护,而微软违反了《谢尔曼法案》的第二条。(*60.参见United States v.Microsoft Corp.,253 F.3d 34,79 (D.C.Cir.2001) (en banc) (per curiam) (“\[I\]t would be inimical to the purpose of the Sherman Act to allow monopolists free reign to squash nascent,albeit unproven,competitors at will.”)。关于对微软案中“新生竞争”处理的更深入讨论,参见Baker(2019,第8段和第10段)。)
4.3支配地位的扩展
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支配型企业将其控制权扩展至邻近市场,利用其支配地位带来的势力削弱或消灭这些市场中的独立竞争对手。这种类型的排他行为令人担忧,既是出于相邻市场竞争的考虑,也是因为相邻市场的强大竞争对手往往是核心市场最有效的实际和潜在进入者。
有许多关于损害的经济学理论可以支持对市场势力从基本市场延伸至相邻市场的担忧。例如,卡尔顿和沃尔德曼(Carlton and Waldman,2002年,第4部分)表明,支配型企业可以将其市场势力“转移”到一个新兴市场,方法就是将其主要产品与一种互补产品捆绑在一起,该互补产品就可以作为进入新兴市场的跳板。维克斯(Vickers,2010)讨论了许多关于损害的其他理论,这些理论都与将知识产权从一级市场扩展到二级市场有关。其中一个理论与“前置”效应(front\|loading effect)相关,西格尔和温斯顿(2007)对此有过研究。其他理论适用的情形是,在位企业从事“基础”创新,而竞争对手可能从事“后续”创新。(*61.关于累积性创新的更多讨论,参见Scotchmer(2004),第5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成功的后续创新者会威胁在位企业在其主要市场上的地位,那么支配型企业就有激励为基础创新的许可设置条件以阻碍后续创新。事实上,即使后续创新者拥有可以加速创新的独特资产,对被取代的恐惧也可能导致在位企业干脆拒绝授权给后续创新者。在这种情形下,相关的理论取决于将创新(或进入)与邻近市场联系起来的机制以及支配型企业在一级市场保护当前市场势力的激励。(*62.可参见Choi and Stefanadis(2001),以及Fumagalli and Motta(2018)。)在相邻市场中,网络效应的存在可以使支配型企业的排他性策略特别有效,因为被网络排除在外可以直接降低竞争产品的吸引力(可以参见Carlton and Waldman,2002;Katz,2018)。
当前,欧洲关于拒绝知识产权许可的判例涵盖了支配型企业利用其市场势力向邻近市场施加影响的情形。这类判决力求保留一级市场的创新激励,又不过度扭曲竞争对手从事创新和/或进入相邻市场的激励。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在某些“例外情况下”,支配型企业有责任将知识产权许可给竞争对手,其中包括了如下情形:获得知识产权对二级市场的有效竞争不可或缺,而且拒绝给予许可会阻碍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的出现。(*63.对于相关讨论,参见欧盟委员会(Guidance on the Commission's enforcement priorities in applying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to abusive exclusionary conduct by dominant undertakings, 2009年2月,第75—90段)。)美国反垄断法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
欧洲有关拒绝交易的法律被适用于影响深远的微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一案。(*64.参见欧盟委员会微软案COMP/C-3/37.79,2004年3月24日的决定。欧盟委员会的决定在2007年得到欧洲初审法院的支持(初审法院的判决,2007年9月17日,案件T-201/04)。法院支持欧盟适用拒绝交易的法理。Vickers(2010)讨论了法院对微软的判决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根据欧盟委员会的陈述,微软将其在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方面的市场势力扩展到了相关的工作组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欧盟委员会认定,为了实现该目的,微软降低了工作组服务器操作系统的竞争供应商获得的互操作性信息(interoperability information)的质量。其结果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微软在该市场的地位显著提高。虽然,在法律上,欧盟委员会的判决依据的是欧洲关于拒绝交易的流行判例,即IMS Health案和Magill案,但它也讨论了微软有什么激励采取“防御性杠杆”(defensive leveraging)以保护它在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中的市场势力。(*65.Kuhn and van Reenen(2009)认为,与美国的情况相比,关于防御性杠杆的考虑与微软工作组服务器的情况更为相关,因为竞争对手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可以向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公开大量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欧盟对微软案要求的救济措施是,微软有义务以非歧视性的合理条件向竞争对手披露特定的互操作性信息。(*66.欧盟委员会在2008年2月发现,微软没有履行这一义务,仍对访问接口文档收取不合理的专利费。这一决定于2012年6月得到卢森堡综合法院的支持(综合法院的判决,2012年6月27日,案件T-167/08)。关于在这种情况下的救济措施的讨论,参见Kuhn and van Reenen(2009)。)
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没有可以比较的垄断扩展案例。(*67.上诉法院将此案发回地方法院审理后,美国司法部对微软提起的诉讼被撤销。)这可能反映了美国与欧盟对可以将垄断势力延伸至邻近市场的单边行为有不同处理,而这种不同尤其体现在,欧盟要求提供开放的接口以及公平对待相邻市场的竞争对手。(*68.美国的最终判决要求微软披露Windows使用的通信协议。这种补救措施与恢复PC操作系统市场的竞争有关,并不反映微软的独立违规行为。)
限制支配地位扩展的一个常见建议是,要求支配型企业在相邻市场中为竞争对手提供非歧视性的进入条件。当支配型企业干脆拒绝让竞争对手与其优势产品交互连接或交互操作时,就会出现歧视性进入的极端情况。通过反垄断执法强制推行竞争对手的非歧视性进入,可能需要解决几个棘手的问题,包括关于“合理”接入费的经济问题,以及关于兼容性和接口设计的技术问题。如果核心产品或邻近产品由于技术进步而迅速变化,那么这些问题就特别具有挑战性。事实上,在受监管的行业,特别是在电信行业,主要负责处理这些进入问题的是专业部门的监管者,而不是竞争监管当局。
尤其是考虑到公众对数字平台的社会作用有强烈兴趣,当今最紧迫的问题是,对于为一个庞大的经济生态系统提供基础的平台,应当对其所有者适用什么样的政策。这是一种与以前有所不同的新情况:如何保护和促进一个可能与其他平台竞争的专有平台上的内容或应用程序之间的竞争。如果一种互补品或互补服务的供应商因在专有平台上处于不利地位而面临重大损害,那么该平台的所有者就可能拥有巨大的经济势力。消费者是否受损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平台所有者的政策是否会增加平台对于用户的总价值,互补品的替代品之间的竞争性质,以及离开平台的能力(这是平台之间实际竞争程度的函数)。在这一领域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为了获取更多租金而试图减少互补品租金的平台。我们可以推断,随着时间的推移,租金份额的这种变化将影响平台和互补品的创新回报,从而影响创新的数量。(*69.关于这一点的更详细讨论,参见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斯蒂格勒监管中心的“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Digital Platforms: Market Structure and Antitrust Subcommittee Report”,该报告于2019年5月15日在数字平台会议上发表,可见https://research.chicagobooth.edu/\|/media/research/stigler/pdfs/market\|structure\|\|\|report\|as\|of\|15\|may\|2019.pdf?la=en&hash=B2F11FB11 8904F2AD701B78FA24F08CFF1C0F58F。)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会发现,对这种情况的干预尤其困难,因为美国法院反对给交易施加任何义务,而且它们尊重财产权。然而,甚至在Trinko案之后的Aspen Ski和柯达的案件中,改变自愿达成的交易仍可能承担反垄断责任。然而,目前的美国最高法院是否会支持这一责任理论,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很可能是未来几年最重要的反垄断问题之一。对于在专有数字平台上运营的企业,如果法院在美国解释反垄断法时,主张只提供很少的保护,或者根本不提供保护,那么许多这样的企业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而且它们可能会与消费者联手,要么争取修改美国反垄断法,要么争取对大型数字平台实施某种形式的监管。(*70.关于可能增加竞争的法规的讨论,参见Stiger Report(2019)。)美国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已经提议对大型数字平台进行拆分和监管。(*71.Elizabeth Warren(2019),“Here's How We Can Break Up Big Tech”。)■
(中国政法大学黄健栓译)
参考文献
Aghion,Philippe,and Peter Howitt (1992),“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Econometrica,60,323-351.
Aghion,Philippe,and Rachel Griffith (2005),Competition and Growth: Reconciling Theory and Evidence,Cambridge,MA: MIT Press.
Aghion,Philippe,Cristopher Harris,Peter Howitt and John Vickers (2001),“Competition,Imitation and Growth with Step-by-Step Innova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68,467-492.
Aghion,Philippe,Nick Bloom,Richard Blundell,Rachel Griffith and Peter Howitt (2005),“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0(2),701-728.
Amelio,Andrea,Thomas Buettner,Cyril Hariton,Gábor Koltay,Penelope Papandropoulos,Geza Sapi,Tommaso Valletti and Hans Zenger (2018),“Recent Developments at DG Competition: 2017/2018”,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53 (4),653-679.
Arrow,Kenneth (1962),“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o Invention.” In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467- 92,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ker,Jonathan (2019),The Antitrust Paradig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aker,Jonathan (2007),“Beyond Schumpeter vs.Arrow: How Antitrust Fosters Innovation”,Antitrust Law Journal,74.
Boik,Andre and Kenneth Corts (2016),“The Effects of Platform MFNs on Competition and Entry”,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59 (1),105-134.
Bourreau,Marc and Bruno Jullien (2018),“Mergers,Investments and Demand Expansion”,Economics Letters,167,136-141.
Bourreau,Marc,Bruno Jullien and Yassine Lefouili (2018),“Mergers,and Demand-enhancing Innovation”,TSE Working Paper,18-907.
Bourreau,Marc and Alexandre de Streele (2019),“Digital Conglomerates and EU Competition Policy”,Report for CERRE,March.
Bresnahan,Timothy,Shane Greenstein,and Rebecca Henderson (2012),“Schumpeterian Competition and Diseconomies of Scope: Illustrations from the Histories of Microsoft and IBM,” in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Revisited,Josh Lerner and Scott Stern,eds.,NBER.
Crémer,Jacques,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 and Heike Schweitzer (2019),“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ial Era”,Report fo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Carlton,Dennis and Michael Waldman (2002),“The Strategic Use of Tying to Preserve and Create Market Power in Evolving Industries”,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33(2),194-220.
Chen,Yongmin and Marius Schwartz (2013),“Product Innovation Incentives:Monopoly vs.Competition”,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22(3),513-528.
Choi Jay Pil and Christodoulos Stefanadis (2001),“Tying,Investment and Dynamic Leveraging Theory”,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32(1),194-220.
Christensen,Clayton (1997),The Innovator's Dilemma.
Chugh,Randy,Nathan Goldstein,Eric Lewis,Jeffrey Lien,Deborah Minehart and Nancy Rose (2016),“Economics at the Antitrust Division 2015-2016:Household Appliances,Oil Field Services,and Airport Slots”,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46,535-556.
Carlton,Dennis and Ralph Winter (2018),“Vertical Most-favored-nation Restraints and Credit Card No-surcharge Rules”,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61(2),215-251.
Cunningham,Colleen,Florian Ederer,and Song Ma (2019),“Killer Acquisitions,” mimeo,available at http://faculty.som.yale.edu/songma/files/cem_killeracquisitions.pdf.
d'Aspremont,Claude and Alexis Jacquemin (1988),“Cooperative and Non-cooperative R&D in Duopoly with Spillover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8(5),1133-1137.
Denicolò,Vincenzo and Michele Polo (2018),“Duplicative Research,Mergers and Innovation”,Economics Letters,166,56-59.
Farrell,Joseph and Carl Shapiro (2010),“Antitrust Evaluation of Horizontal Mergers:An Economic Alternative to Market Definition,” Berkeley Economic Journal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Policies and Perspectives,10.
Federico,Giulio (2017),“Horizontal Mergers,Innovation and the Competitive Process”,Journal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 Practice,8(10),668-677.
Federico,Giulio,Gregor Langus and Tommaso Valletti (2017),“A Simple Model of Mergers and Innovation”,Economics Letters,157,136-140.
Federico,Giulio,Gregor Langus and Tommaso Valletti (2018),“Horizontal Mergers and Product Innov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59,1-23.
Fumagalli,Chiara and Massimo Motta (2018),“Dynamic Vertical Foreclosure”,mimeo.
Gans,Joshua (2011),“When is Static Analysis a Sufficient Proxy for Dynamic Considerations? Reconsidering Antitrust and Innovation”,in Josh Lerner and Scott Stern (eds),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Volume 11,NB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ans,Joshua (2016),The Disruption Dilemma,MIT Press.
Gilbert,Richard (2019a),“Merger Enforcement for Innovation:Examples and Lessons for Remedies,” mimeo.
Gilbert,Richard (2019b),“Competition,Mergers and R&D Diversity”,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54(3),465-484.
Gilbert,Richard,Christian Riis and Erlend Riis (2018),“Stepwise innovation by an oligopol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61,413-438.
Gilbert,Richard and Hillary Greene (2015),“Merging Innovation into Antitrust Agency Enforcement of the Clayton Act”,The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83(6),1919-1947.
Gilbert,Richard (2006),“Looking for Mr.Schumpeter:Where Are We in the Competition Innovation Debate?”,Chapter 6 in Adam Jaffe,Josh Lerner and Scott Stern (eds.),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Volume 6,159-215.
Gilbert,Richard and Steven Sunshine (1995),“Incorporating Dynamic Efficiency Concerns in Merger Analysis:The Use of Innovation Markets”,Antitrust Law Journal,63,569-601.
Gilbert,Richard and David Newbery (1982),“Preemptive Patenting and the Persistence of Monopol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2(3),514-526.
Greenstein,Shane andGarey Ramey (1998),“Market Structure,Innovation and 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6,285-311.
Haucap,Justus,Alexander Rasch and Joel Stiebale (2019),“How Mergers Affect Innovation:Theory and Evide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63,283-325.
Hill,Nicholas,Nancy Rose,and Tor Winston (2015),“Economics at the Antitrust Division 2014-2015:Comcast/Time Warner Cable and Applied Materials/ Tokyo Electron”,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47,425-435.
Hovenkamp,Herbert and Carl Shapiro (2018),“Horizontal Mergers,Market Structure,and Burdens of Proof”,The Yale Law Journal,127(7),1996-2025.
Igami,Mitsuru and Kosuke Uetake (2019),“Mergers,Innovation,and Entry-Exit Dynamics:Consolidation of the Hard Disk Drive Industry,1996-2016”,mimeo.
Jullien,Bruno and Yassine Lefouili (2018),“Horizontal Mergers and Innovation”,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14 (3),364-392.
Katz,Michael (2018),“Exclusionary Conduct in Multi-sided Markets”,in OECD,Rethinking Antitrust Tools for Multi-Sided Platforms.
Katz,Michael and Jonathan Sallet (2018),“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The Yale Law Journal,127(7),2142 - 2175.
Katz,Michael,and Howard Shelanski (2005),“Mergers Policy and Innovation:Must Enforcement Change to Account for Technological Change?”,in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vol.5,edited by Adam Jaffe,Josh Lerner,and Scott Stern,109- 65.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ühn,Kai-Uwe,Szabolcs Lorincz,Vincent Verouden and Annemiek Wilpshaar (2012),“Economics at DG Competition,2011-2012”,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41,251-270.
Kühn,Kai-Uwe and John van Reenen (2009),“Interoperability and Market Foreclosure in the European Microsoft Case”,in Bruce Lyons (ed.),Cases in European Competition Policy.The Economic Analysis,50-7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woka,John (2018),“Reviving Merger Control:A Comprehensive Plan for Reforming Policy and Practice,” American Antitrust Institute,available at https://www.antitrust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18/10/Kwoka-Reviving-Merger-Control-October-2018.pdf.
Letina,Igor (2016),“The Road Not Taken:Competition and the R&D Portfolio”,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47(2),433-460.
Loertscher,Simon and Leslie Marx (forthcoming),“Merger Review for Markets with Buyer Pow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Lopez,Angel and Xavier Vives (forthcoming),“Overlapping Ownership,R&D Spillovers,and Antitrust Polic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Marshall,Guillermo and Alvaro Parra (2018),“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The Role of the Product Market”,mimeo.
Mermelstein,Ben,Volker Nocke,Mark A.Satterthwaite,and Michael D.Whinston (forthcoming),“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Growth in Industries with Scale Economies:A Computational Model of Optimal Merger Polic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Motta,Massimo and Emanuele Tarantino (2018),“The Effect of Horizontal Mergers,When Firms Compete in Prices and Investments”,mimeo.
O'Brien,Daniel and Steven Salop (2000),“Competitive Effects of Partial Ownership:Financial Interest and Corporate Control”,Antitrust Law Journal,67,559-614.
Reinganum,Jennifer F.(1989),“The Timing of Innovation:Research,Development,and Diffusion”,Chapter 14 in Richard Schmalensee and Robert D.Willig (eds.),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Volume 1,849-908.
Romer,Paul (1990),“Endogenous Technical Chang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4,1002-1037.
Rubinfeld,Daniel and John Hoven (2001),“Innovation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in Jerry Ellig (ed.),Dynamic Competition and Public Policy:Technology,Innovation and Antitrust Issu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h,Raaj Kumar and Joseph Stiglitz (1987),“The Invariance of Market Innovation to the Number of Firms”,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8(1),98-108.
Salop,Steven (2017),“An Enquiry Meet for the Case:Decision Theory,Presumptions,and Evidentiary Burdens in Formulating Antitrust Legal Standards”,mimeo.
Schumpeter,Joseph (1942),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Harper.
Segal,Ilya and Michael Whinston (2007),“Antitrust in Innovative Indus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7(5),1703-1730.
Shapiro,Carl (2003),“Antitrust Limits to Patent Settlements”,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34(2),391-411.
Shapiro,Carl (2010),“Merger Guidelines:Hedgehog to Fox”,Antitrust Law Journal,77,701-759.
Shapiro,Carl (2012),“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Did Arrow Hit the Bull's Eye?”,chapter 7 of Josh Lerner and Scott Stern (eds.),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Revisited,361-404.
Shelanski,Howard (2013),“Information,Innovation,and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Internet”,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61,1663-1705.
Stigler Center on Regul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Digital Platforms,Market Structure and Antitrust Subcommittee Report,15 May 2019,available at https://research.chicagobooth.edu/-/media/research/stigler/pdfs/marketstructure---report-as-of-15-may-2019.pdf?la=en&hash=B2F11FB118904F2AD701B78FA24F08CFF1 C0F58F.
Tirole,Jean (1998),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Cambridge,MA:MIT Press.
Vickers,John (2010),“Competition Policy and Property Rights”,The Economic Journal,120,375-392.
Vives,Xavier (2008),“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 Pressure”,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56(3),419-469.
Werden,Gregory (1996),“A Robust Test for Consumer Welfare Enhancing Mergers Among Sellers of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44,409-413.
Whinston,Michael (2012),“Comment” on Chapter 7 of Josh Lerner and Scott Stern (eds.),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Revisited,404-410.